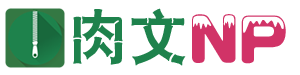绝嫁病公子 作者:卿汀月
绝嫁病公子 作者:卿汀月
第五十八章 南衣遗信
昨夜,顾九将药熬好后就给寡月端去,督促他服了。
她凝着寡月,一瞬间又想到了什么,心头难免一震,抬眼,她似是想说什么,终究是只字未提。
转身欲要离去的时候,那少年突然紧握住她的手,牵着她往正堂而去。
寡月在正堂的一处带锁的柜子里头取出一物,青布包裹着,顾九凝着眉,盯着寡月,见他将那青布拆开,就瞧见那布裹着的一个冰冷的牌位……
寡月将那牌位放在桌案正中,顾九会意过来赶紧将大门和侧门全都掩得严严实实的。
内只燃了一根烛火,顾九将墙角的火盆端了过来。
九月末,十月初。是南衣的忌日。二人都没有特意的记住那个伤心的时日,只记得每每这个时候,连天气都会一转阴沉。
火盆里头的几块孤零零的炭火被顾九用废纸点燃了,这时候寡月从桌案的柜子里头取出一包裹,包裹之中的冥纸被他取出,一沓一沓的散开来。
二人沉默不做声,将那冥纸一张一张的放进火盆之中。
火光映着二人的容颜,青涩稚嫩之中带着一丝超脱年龄的沧桑之感。
二人都将想说的话,一遍一遍的在心里说给南衣听。
火盆中的火光燃尽,香台里的香柱落了一地的灰,顾九扶着寡月坐,整个正堂因为封闭,香烟都弥漫在空气里,连顾九都觉得不好受,她担忧地望着一直以湿帕子捂着鼻口的阴寡月。
她知道,不等香柱烧尽,他是不会去将南衣的牌位移开,更不会离开这里的。
这个人,有时候固执执著的可怕。
香柱终于烧尽了,顾九动了动身子,想去替寡月收拾,一只温柔却暗含力量的手搂住她的腰肢,那人就这么紧紧低将她搂住。
她的身子也因站不稳坐进他的怀中。
少年将脸深深地埋进脖颈处,这一刻,她能清楚的感受到他的脆弱……
南衣的离世,也是他此生难以跨越的沟壑啊。他背负着的重任,他要面对的将来,或者,还有他与南衣的身世牵连……这一切的未知,让人恐慌却又期待……
坐了很久,寡月终于不适应的咳嗽起来。
这才允了顾九将南衣的牌位收拾好后,扶着他出去。
从正堂里出来,子夜的苍穹,果然飘起了纷纷扬扬的细雨,长廊外秋风肆虐……
本以为这样的天气,只能出现在江南的十月,没有想到,长安亦如是。
她扶着他走过长廊,一步一步,腰间的玉佩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,而她无比满足于此刻的拥有。
繁华之后,有一个人守护着你的寂寞,与你一起山河永寂。
一笑倾城,惊才艳艳皆是虚无。
房间越来越近了,那人的步子放慢来,温润的手搭在顾九手上,低垂着的眉眼,纤长的睫羽轻颤,偏头,无比餍足的温柔一笑。
只需一眼,方才悼念南衣的悲伤情绪散去不少。
他似深叹一口气,又是一年春去秋来。
次日,一个微雨的天气,庭院之中的花草树木都笼罩着一层氤氲的烟色。
天还没有亮,一身鹅黄色裙裾的顾九,着木屐拉开门,揉了揉惺忪睡眼,瞧了一眼庭院的雨景。
这样的天气不觉得寒冷,但凉意渐起,她深嗅了一这难得的雨后好空气。
这时候正瞧着两个人撑着伞急急忙忙地朝着这方赶来。
她和寡月的房间是挨在一起的,但明显两人没有注意到她,步履匆忙地朝着寡月房里走。
出了什么急事吗?
等两人站在长廊里收了伞,顾九才看清一个是小易,还有一个是卫簿。
今日寡月是要早朝的,顾九正思考着是要去厨房瞧瞧小宁远是否将早膳和汤药做好了?还是要过去打听到底出了什么事情?
顾九正要朝寡月房里走的时候,便瞧见小易已从寡月房里出来,带上了门。
小易瞧见了她,尴尬地笑道:“九姑娘晨安。”
“晨安。”顾九回了一句,方觉得当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,于是随着小易朝厨房走去。
——
房里。寡月还来不及穿衣裳,就接过卫簿递来的两封信。
是郑裕安和卫箕的来信。
按理因先开母亲的信,可寡月照例先开卫箕的。
卫箕的信中大致意思是说,二夫人要随着他来长安,若是不带上二夫人,二夫人不让他走,然后问了一他们的情况。
寡月收好信,眉头深拧着,郑裕安怕真是等不及了。她或许是想着靳南衣已为朝中三品要臣,靳公府又怎能不让她这个生母进门?
寡月凝着郑裕安的那封信,顿了一会儿后才匆匆拆开。
他早知心中当是催促之语,所以匆匆看罢,可是信至最终的时候,郑裕安却提及,南衣年少之时,靳云湛曾留给他一本书册的。
一本书册?
寡月震了一,为何南衣从未跟他提及过?
寡月匆匆将信件收拾好,转身,凝着身后的卫簿,沉声问道:“靳云湛曾赠过南衣一本书?”
卫簿被寡月这副神情唬了一,想了一后,忙道:“是有一本书,是老爷最后一次离开江南前给公子的,那本书当时二夫人找公子要,公子没给,所以二夫人记着好多年的,那次走后,老爷回长安没多少日子就听说……”
卫簿也纳闷这事情公子怎么没有同主子说呢?
寡月觉得南衣不可能不告诉他,在他困惑不已的时候,寡月想起了南衣临死前同他说的话,在困惑无比的时候,莫要忘了我留给你的几封信。
寡月快步的走到床榻前,将枕头底,昨夜沐浴之前,自己一直随身携带的红布包取出来。
这是南衣留给他的信件,其中一封三年前的华胥楼给了慕华胥。
寡月拆开红布包,才发现剩的三封信只剩一封颜色深褐色,一看便是有些年月,那信封上的字迹也不像是南衣的……
他心头一紧,正犹豫着要不要打开。
之前是因慕七,他想起南衣留给他的此物,如今再回想起来,莫名有些后怕自己忍不住将这信封全部拆开。
南衣说过,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拆开信件,而他也不懂这万不得已是什么时候。
他正天人交战着,犹豫是否要打开这封信,就打开这一封信可好?
寡月将剩的几封信收好,手中一直拿着那封已成深褐色,字迹都略显斑驳的信件,久久地,不知如何是好……
站在一旁的卫簿走上前来道:“主子……不若打开来一瞧吧。”按理公子不会特意遗忘将这事告知主子的,除非是另有隐情,公子参透命理,便是知晓一切都是随遇而安,等着主子去发现吧……
寡月低垂着凤眼,目光久久地落在手中的信笺上,他意识地认为这封信当是靳云湛留给南衣的。
卫簿站在一旁都干着急着,看着主子的样子他心中也难受得紧。
许久,少年似是余光瞧了眼外头的天色,才用指尖挑开那因时日已久都有些黏粘在一起的封口。
泛黄的纸张被展开,一个一个风流恣意的字体跃然于目,笔锋之中却带着些许虚弱的牵强……
少年清澈的眉目,麋鹿一般的温润光芒黯淡来,一丝惊惧一闪而过后,凤目阴鸷,眸深似海……
他似乎是匆匆的将信放在床榻上,然后伸手拿起屏风上搭着的衣服,十分迅速地穿好后,再将那封信贴身收拾好。
“卫簿,你回紫藤居去,回信卫箕一封,言:要他再多等几日!”寡月匆匆地吩咐道,往正堂那处走去。
顾九也瞧见了,今日的寡月很是匆忙,他几乎是匆匆的用完早膳,没有等上一刻钟,便将药也用了。
顾九真有些担心他会消化不良,一面她给他打包着他要带在身上的吃食,一面她又匆匆叮嘱几句要他早些回来,再就是她今日要回隐月阁一趟。
顾九匆匆换了男装,将寡月送出府宅,给他匆匆整理了一衣袍,看着他上马车,顾九便撑着伞离开……
因为雨,顾九觉得受过伤的那只腿骨有些刺痛,她转身没有走几步,马车上的少年一挑车帘,急切低叮嘱了一句:“注意安全,早些回来……”
顾九讶异地回眸,盯着寡月,瞥见他眼中那抹深意,茫然地颔首。
她知道,他要在他回来的时候,瞧见她在园子里,只有这样他才心安。
她还知道,萧肃就跟在她身后不远,只是不想出声打扰她而已。
“吱呀”一声车轮转动,马车与她擦肩而过,她突然觉得今日的寡月有心思,不知是怎样的心思,但是她能从他的眉心读出他的坚定……
顾九走到隐月阁的时候,似乎听见对街的客栈还有一旁的茶肆、棋楼、书楼里,似乎是在谈论什么。
因为她听到靳南衣三个字不免驻足。
不出意料,谈论昨夜春香苑诗会的人很多,昨夜三个女子的诗句也被许多人争相抄录,当然她与萧槿的那场对决也被无数人谈论。
顾九突然想起现在月初,那本她追着的话本是否这个月该出新的了?
想着她撑着伞朝前头的一家书楼里走去。
书楼处楼里楼外都聚集着不少书生,关于昨夜她与萧槿的“对决”,这里谈论的也煞是激烈。
昨夜的诗词,还有后来的对子都被书楼的掌柜命人写来,以画轴的形式挂在了外头……
“萧大人的几个上联都是出的极好的。”
“昨夜的诗会,没有瞧见真是遗憾,不过我站在春香苑外也是听得清楚了的。”
那些人的闲聊声被顾九抛之脑后,她选了新到的话本后走到掌柜那处正欲要付钱离开,却听得书楼正门口有几个书生正在谈论什么……
“靳学士不是夫人谢珍所出吗?怎么成了庶出的了?”
“你们不知道吧,今儿个出门的时候就听人谈论,靳南衣是庶出的,不是谢珍所出,算是寄名,听说他生母在江南。”
“什么?如此一来靳学士莫非是弃了生母侍奉嫡母?这也太……”
“是啊,将自己生母丢在江南,而侍奉嫡母,这也太不厚道了吧!”
“无非是谢家的家世,呵!也难怪看不上萧大人,原来是有华胥楼主这金主,我看这靳南衣就是一个见利忘义的小人!”
顾九脸色愈来愈阴沉,维护大雍萧府的人不在少数,靳南衣也自然被一些人“鄙夷”。
她更没有想到,这么早寡月担心的事情就传了出来。
“公子,这话本您还……”掌柜的见顾九半天没回过神来忙问道。
顾九怔了,忙去摸钱袋,放一吊钱后她拿着书面色复杂的离开了。
——
这一整天寡月都很忙,十一月皇家冬日狩猎要开始了,虽说如今大雍大部分的兵力都在西凉,可是每年皇家的狩猎是少不了的。
冬日祭与狩猎差不多在一个月,此次狩猎和祭祀,给寡月的感觉如此微妙,总觉得不会是这么寻常而已。
他担心身在西凉的夜风,许久没有传来消息了,若是西凉已平,那大雍的军队也要班师返朝了,久不闻音讯,或许是因为还有许多残余势力要处理。
又或者……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。
想到这里,寡月本在写着祭文的手又是一抖,若真如他所想,狩猎和冬日祭更多的是为了给班师回朝的军队接风洗尘,那现在远在祁连的军队已经开始整装了。
大雍撤兵不得向西凉人透露,这军机知道的人也不会多。
只是,夜风会回朝吗?那个人会回朝吗?留守西凉的又会是谁?
因突然而来的诸多困惑,寡月暂时压了去靳公府的打算,一忙又是到申时过了才离开翰林院。
——
次日的时候,还真有许多高官因着靳南衣的身世派人去城南靳公府里头去打听。
长安这地方的人,一有什么事情传出来,便是闹得满城风雨,无聊的人也比比皆是。
钟翁听得有一群人上门来问,不禁骇了一大跳。
命小厮们将人打发走,掩上大门,神色匆匆地去松景楼寻靳公。
钟翁将这事同靳公一说,靳公当即变了神色。
正堂里头,靳家几房都被丫鬟婆子们唤来。
这时候正午将过,谢珍两姐妹正打算眯午觉,这会儿被婆子们请来心里自是有些怨言的。
梨木大椅,猩红的椅垫子,谢珊歪躺着,手里把弄着杯盏,一双儿女坐在更手的位置上,靳素宜与自家的丫鬟聊着新来的丹蔻,将那嫩如白葱的手撑得老直了,美目眯着欣赏着丹蔻的颜色。
靳素熙静坐在一旁品着茶,脑海里回味着夫子今日早晨的讲解的句子,并把昨天要记背的东西在脑海里过了一遍。
谢珍坐在左侧头椅上,面色安详,若有所思的样子,琼娘站在她身后,有意无意的把玩着手腕上的翡翠镯子,那是她昨日将去打的,带着正欢喜。
这时候靳公从门外走进,由钟翁扶着。
老人神色凝重,阴沉着脸。
靳素宜觉得气氛有些不对,赶紧将那双白皙玉手掩进了袖子里。谢珊也察觉到了,坐正了身子。
钟翁将靳公扶到上座上坐后,还没有往旁侧走两步,就听到两声拐杖捣地的声音。
这一来众人都惊惧了一,望向靳公。
“是谁将南衣的事情说出去的?”老人扫视众人一眼,这时候靳云涛将将从外头回来,正巧听到这么一句。
靳云涛将从外头回来,也自是听到外面在说些什么,不由的他慢步伐。
靳长儒听到脚步声,抬眼一望正对向靳云涛的眼。
“父亲。”靳云涛朝靳公作揖,靳公神情放柔了些,点点头,示意靳云涛就坐。
“父亲出了何事?”靳云涛这一句很明显是试探也是确认,他到底不知道有人都问到府上来了。
靳长儒凝了靳云涛一眼,指了指钟翁示意他说。
钟翁上前道:“二爷,两位夫人,今晨有几家的人来问南衣少爷的身世了……”
如此一来,连谢珍的神情都起了变化。
靳素宜听到靳公那句“是谁将南衣的事情说出去”的时候心中就惊骇了一瞬,如此一来连身子都颤了一,看来前日春香苑到底是有人听到了……
她终究是不懂在那种地方说错话有多大的后果,现在却头次懂了,以前她住在汾阳,不知道长安是什么样子,也只是小时候随着母亲和大娘来长安去找表姐们的时候来过几趟。
旁人未注意到靳素宜的神情,离得她最近的兄长靳素熙是注意到了的。
当即就料到这丫头定是在外头说漏了嘴,无奈摇头叹了一声。
正巧这时候堂里又传来靳公一声呵斥:“我在汾阳的时候就说过,南衣的身世若是有人敢传出去,那便将靳郑氏接回来!”
靳公如此一说,在场的人都骇住了,谢珍更是瞪大了眼睛。
“靳公……”谢珍竟是从梨木大座椅上腾地站起,“自禀德十三年春得知靳南衣出汾阳靳公府以来,他靳南衣的身世又有多少人严查?他从江南轩城入科举,他的事情难道没有人查吗?靳南衣的身世能被人查出既在情理之中,难道靳公让那害我孩子的贱人入府,是早有谋划?!”
“大夫人!”钟翁惊恐地唤了一声,连着站在门口的几个婆子也骇了一跳。
“谢珍,我早前就说过,南衣的名声比什么都重要,他如今为翰林三品,身系靳公府一门荣辱,你既然嫁入我靳公府就要听靳公府的,这里不是谢府,本公不是没有给你们提过醒,不是我有心偏袒郑氏,而是如今的形式已发展到这一步,既然有人上门来问南衣身世,说不定当年郑氏之事没几日就会为众人所知!”
“就因为那个贱人生的孩子,您就要将那贱人接回来吗?!我才是靳云湛的原配嫡妻!靳云湛他一日没有休我,我便是他的妻子,我谢珍不同意,谁也甭想让那靳郑氏进门!要同意让靳云湛亲口来跟我说!”
青绿色锦袍褐色襦裙的女子厉声说道,她气息不稳,也不曾顾及到形象,一口一个“贱人”,她双目通红显然已是气急。
靳公的脸色更难看,谢珍无疑是拿捏的很准的,如今整个靳公府打理着的还是她谢珍,她的堂妹谢珊她能不了解成日里喜欢乱花银子赌瘾甚大,靳公年事已高,靳云涛又是个懦弱的,靳素熙虽不随他父母是个有计较的但年事尚小,整个宅子里头还是得指望她打理。
况且这么多年,她谢珍也没出过什么差错。
靳公的面色难看至极,方才那一番话显然靳公也是气急而言,若是他真有心接郑氏回靳公府,那日便同南衣说了。只是想到府中人不把他的命令当一会儿事,所以才说让郑氏回府!
若郑氏不回府,这身世之事又闹得满城风雨,他又要如何同南衣说?
而这谢珍竟然说要接郑氏回府,便让靳云湛亲口同她说!
这不是明摆着膈应他?他白发人送黑发人,一个年迈鳏夫,已是晚年凄惨,这谢珍又提起他心爱长子,不是故意让他心里难受?
靳长儒倒吸一口凉气后又深吐了出去,胡子都有些吹起。
如此氛围,靳二爷房里的都不再说话了,靳素宜脸压的低低的,倒是靳素熙清秀的脸上一脸平静。
这时候钟翁上前一步,朝着谢珍柔声道:“大夫人,靳公也不是想接纳郑氏回来的……只是您想想如今这种形式,要南衣少爷如何做人?若是传出他生母在江南寡居,对南衣少爷,对靳公府都不好不是么?老爷只是一时气急才那般说的……”
谢珍余光白了一计钟翁,她没想着置那母子于死地了,他们便来得寸进尺了?想要名分?门都没有!
大不了玉石俱焚,她十四岁嫁到靳公府,得到了什么?
丈夫死了,她连个孩子都没有,守着贞洁不得改嫁,便是帮他打理靳公府,春去冬来便是二十年!如此也只能换来一个死后与他同穴,是的,生同寝死同穴,若是郑氏不入靳公府,二夫人的身份不得众人承认,与靳云湛同穴的便也只有她一人……
她一生到最后,也只是为了与他靳云湛同棺而葬!
她得到了什么……
便是十四岁,喜帕被挑起的那一眼,害了她一生,他纳妾,她忍痛同意了,他死了,而她这个未亡人思念了他十多年……
“不!我绝不会同意郑氏回来!”谢珍嘶声一吼,拂袖而去,眼眶俨然已有些发红。
让郑氏回来日日让她想起死去的孩子吗?让她回来斗到死了还和她争丈夫吗?
正堂的门框处,众人只看到谢珍孤傲间却显得无比萧条的身影。
琼娘瞧了一眼众人,朝靳公深作一揖后跟了出去。
靳公气得发抖了胡子抖了两后没有再抖了,反而目中多了一丝惆怅,他朝着二爷房里的人一扬手,示意他们退。
“都退吧。”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。
靳云涛将儿子送到书房去了,因靳素熙午还有学业。
谢珊一出了松景楼就领着靳素宜往谢珍的香桂园走。
“娘,我不去了。”靳素宜眸光狡黠一闪说道。
“怎么不去了?你姨生气了你不去?她不光是你你姨还是这宅子里头的大娘……”谢珊拉着靳素宜往香桂园走。
“娘,你说姨都在气头上你往上贴个什么劲儿?我不去了,我还有事情。”靳素宜一个劲儿地想要将自己的手从谢珊手中抽出来。
“哎,我说你,你怎么……”谢珊的话还没有说完便被突然出现的琼娘打断了。
“夫人、小姐来了就进去吧,大夫人正等着。”琼娘站在石基处凝着二人说道。
二人讶了一,谢珊拉着靳素宜走过石基玉阑干,进了香桂阁。
谢珍歪躺在床榻上,只手撑着额,神色很不好看。
谢珊这才放开靳素宜的手,上前去问道:“姐,你还好吧……我说啊,你也别气了,郑氏回不来的,呵呵呵。”
谢珊话音刚落,谢珍闭着的眼猛地睁开,这一睁眼把谢珊吓了一跳,莫名的谢珊有些害怕。
谢珍却是同一旁的琼娘道:“玉琼,你退。”
“是。”琼娘瞧了一眼谢珍后退。
“吱呀”一声的关门声后,谢珍猛地反握住琼娘的手,沉声道:“谢珊,是你?”
谢珊骇了一跳,猛地后退一步,道:“姐,你说什么?”
“你别装傻!是你将靳南衣的身世传出去的?你就是怕我得了这一便宜儿子,将来不把你家熙儿当儿子?呵!我的好妹妹,你何苦这样算计我?将靳南衣那贱人子的身世传出去了,让那贱人回来了,你们就是这种心思?何苦来算计你亲堂姐!”
谢珍一把将一头雾水的谢珊推开。
她一步一步的靠近:“谢珊,我只笑你愚蠢,我从不把靳南衣当人,你看不出来?我疼他多还是疼你家熙儿多?你们就这般算计我,不顾姐妹之情了?!好啊!真真是好!我谢珍为谢家操劳一生,得你们这般来算计!”
本是被骂蒙了的谢珊也终于听懂了谢珍说的,是说靳南衣的身世是她传出去的?!
“姐!你怎么可以这般说?我好心好意来看你,你把一通恶气全撒我头上?我谢珊再蠢也犯不着将靳公的命令当耳边风,况且给那靳南衣的娘正名对我有什么好处?”谢珊说着也红了眼,“你怎么可以这么想我?都说珍姐姐聪明,原是将聪明劲全算计在姐妹头上了!”
“你……”谢珍气急指着谢珊咬牙切齿,“不是你说的又是谁说的?这事情别人就算是要查也不好查!就连着谢家那头都瞒去了,呵呵,倒是靳府里出了纰漏。”
听着谢珍与谢珊二人的争吵,靳素宜的脸色愈来愈惨白,她迫切地想离开这里,又不想母亲和大娘二人争吵。
这一来大娘心中对她娘肯定起了计较!那日后她与她哥又当怎么办?
她还没有出阁,若是出阁大娘拿的嫁妆少了怎么办?若是她哥不受大娘宠了怎么办?
她终于意识到自己做错了,却是想将这个瞒去,不能让谢珍发现是她说漏了,再说也不一定是她说漏了被人听到了,若是表姐说的呢?她那个表姐可不是个简单的人,就连她都看不出来她那优秀的让她羡慕嫉妒恨的表姐到底想要什么。
反正,一切都是因那靳南衣而起,没有那靳南衣他们一家子都是开开心心的过日子,大娘不会和娘亲吵架,她哥也不会成为她们争执的话题,如此一来靳素宜又对靳南衣生了许多怨怼!
都是靳南衣的错!
“大娘!我想您误会了,我娘怎么可能同外头说这种话呢?您对我和我哥这么好,我娘怎能帮着那靳南衣让他的贱人娘进府呢?”靳素宜绝对是个小小年纪便会见风使舵的人。
一句“对她喝她哥那么好”将谢珍给稳住了,一句“贱人娘”又让谢珍心里头无比痛快。
这小辈倒是个念好的,不光是个念好的呃,还是个醒事的,想着谢珍心中不由一软。或许……不是谢珊说的,只是被人查出来了?看着谢珊平时呆笨好赌了些儿,也不像是个不知分寸的。
靳素宜见谢珍神情松软来,忙上前解开谢珍抓着她娘的手道:“定是叫人给查出来了,这至靳南衣及第以来,他的流言蜚语就没少过,别人查他也在情理中,倒是爷爷也真是的,摆明了有些帮着靳南衣他娘,明知道别人会查出来,还说什么传出去了就让他贱人娘回府!这不心中就是给他娘留了后路。”
靳素宜越是这么说,谢珍越是往这方想,越想越是咬牙切齿,她为靳公府操劳得到了什么?
靳公怎么能如此不仁不义,她没为靳家开枝散叶,没有功劳好歹也有苦劳吧!
“姨啊……”靳素宜娇声一唤,这会儿唤得是她常唤的,先前唤“大娘”是因为谢珍在气头上,按照这宅子里的规矩唤的,她狡黠地眸光一闪,离得谢珍更近了些,“姨啊……素宜听到了一件事儿,觉得还是得同姨说的……”
“嗯?”谢珍给了个反应狐疑地问道。
靳素宜贴的更紧了些儿,她身后的谢珊也凑了上来。
“素宜听说靳南衣在江南有桩婚事!”
“他有婚事与我何干?”谢珍回了一句。
“姨姨糊涂,你现在才是靳南衣的嫡母!”靳素宜赶紧道。
这一句“嫡母”让谢珍心头又是一撞。
“况且他的未婚妻子可是富甲江南的华胥楼主的妹妹!”靳素宜说道,双目打量着此刻谢珍脸上的表情。
谢珍果然一震,之后又皱起眉头。
靳素宜也达到了自己的目的。靳南衣的未婚妻子是华胥楼主的妹妹,无疑是告诉她们靳南衣若是真娶了那女子,便是傍上了金主,无疑是有一个强大支撑的,这无疑是大大的威胁到她哥。而谢珍要是有那个心思,她为靳南衣嫡母,自是可以不同意这桩婚事的。
靳素宜想就算她哥靳公之位没指望,那谢珍不帮忙,也可以找那慕家的敲一大笔嫁妆费用!
靳素宜能想到的,谢珍也自然是想到了的。
见着安静了许久,谢珊动了动身子,上前一步似乎是想开口再提将才的话题,却听谢珍笑道:“珊儿,我将将是急糊涂了,我是无心的,你也别放在心上。”
谢珊听得谢珍此刻松口竟是有些感动,本来就是好姐妹,又有什么一直要放在心里膈应着,她一把拉开靳素宜,上前道:“姐啊,我从来都拿你当亲姐,你自是比我的亲娘对我还好,我在靳家这么多年也是多亏了你,我家熙儿和素宜你都当成自己的亲骨肉对待,我又怎地吃里扒外拖你后腿?姐我绝对不会乱说话的……”
谢珍点点头,心头柔软了些,淡声道:“我也累了,你们都退吧。”
“那好,姐,我便带素宜退了。”谢珊说道,眼圈红着。
——
将入夜的时候,松景楼前又见几个神色匆匆的小厮。
原来是,大少爷回府了。
钟翁不在便是几个小厮来禀的。
将将用了晚饭的靳公在书房里头练字,听得人来禀,就才到靳南衣是为了“身世”一事来的。
搁笔的靳公,久久不给那两个小厮答复,是称病不见,还是说已经歇了?
过了许久,靳公才说道:“你们退就说……本公现在在休息。”
那两个小厮讶了一,领命退了出去。
等那小厮一走,靳公还真躺倒榻上休息去了。末了,等他醒来的时候已是酉三刻了。
起榻时候他唤了一声,进来的是钟翁,他问了一句:“南衣回去没有?”
却听得钟翁愁苦着脸道:“南衣少爷已经在祠堂里跪了一个多时辰了……”
靳公无疑是讶了一,在床榻前坐着,低着头想了许久,才开始慢手慢脚的穿衣。
等将中衣穿好,他站起来,钟翁上前给老人家穿上外袍,正考虑着要不要系腰带。
“我去见他……”靳公叹了一声。
钟翁这才去取腰带还有宫绦玉佩。
——
寡月一直跪在祠堂里,昨日他便想着要来一趟靳公府的,可是昨日今日都太忙了。
他还是来了,靳公却在休息,黄昏时候休息的确说不过去,只有一个原因,靳公也知道了外头的传闻。
如此一来,他不得不赶紧提议了。
祠堂的灯烛很多,方才已有婆子丫鬟来将这里都点亮了,他知道他今天一定要见到靳公。
他可以让郑氏回府,更可以快些让九儿成为他的妻子,让九儿名正言顺的站在他的身边。
方才他奉上的香柱已经燃尽了,一旁站着的一个婆子两个丫鬟已经开始打起瞌睡。
小易一个人在祠堂前的院子里头颇为无聊地把弄着那些花花草草。
正当小易发现这里遍地黄芪的时候,他瞧着两个人朝他这里走来。
小易认出来是靳公和那个老管家。
只是那二人走到那歪脖子老杏树就停住了,小易不禁皱了眉。
看着祠堂里头的耀眼灯火,靳公正踌躇着不敢靠近。
郑氏的事,谢珍那方死咬着不放,更是将他的湛儿都提出来膈应他。
靳家又好不容易出了个三品翰林学士,说出去别人都说他有个号孙子,便是比现在的郑家和杨家都强了好多倍,这郑、杨两家,也好歹是国公府!
如今他汾阳靳氏得以扬眉吐气都指望这个庶出的孙子了,南衣这边他也不得不处理好。
“靳公爷,您要是为难,老奴替您再同南衣少爷说说……可是老奴终是认为,南衣少爷也有南衣少爷的苦,您便是不认他娘,也要认了这些年他寒窗苦读,可是从没话咱们府上一分银子,南衣少爷虽大了素熙少爷几岁,也终究只是个孩子,听人说三岁那年也差点病死了……当然老奴只是随便说说……”钟翁说着低头退后一步。
靳公自是晓得钟翁之意,他不能这样连句话都不回了南衣。
钟翁的意思是总是要面对的,不妨先去回个话,是好是坏,让南衣先安心。
末了,老人抬腿朝着祠堂走去,衣摆拂过十月伏地而声的植被。
祠堂中静跪在蒲团上的白衣少年听闻身后的脚步声,眉间一动,睁开沉郁的凤眸。
------题外话------
票票君……来吧。错别字是后一天改前一天的,可能有时候偷懒推迟几天改正。谢谢钻钻花花票票。
第五十八章 南衣遗信
第五十八章 南衣遗信
同类推荐:
偷奸御妹(高h)、
万人嫌摆烂后成了钓系美人、
肉文女主养成日志[快穿系统NPH]、
娇宠无边(高h父女)、
色情神豪系统让我养男人、
彩虹的尽头(西幻 1V1)、
温柔大美人的佛系快穿、
师傅不要啊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