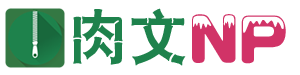再过两天就是衙署封笔的日子,城里城外全是新年喜庆的气氛,燕云歌也是看见这满街的红灯笼才恍惚地想起来,居然小年了。
她一直向前,早已经不记得过年是什么滋味,现在回头看,那些寒来暑往、秋收冬藏,似乎都与她没有关系。
走到城南宅子时,赵灵正站在门口指挥着文香挂灯笼,贴春对,两人看见她来高兴地直招手,文香提着裙子跑来说:“太好了,我正愁我这字拿不出手,还是小姐写吧,省得我给府里丢人。”
燕云歌从恍惚中回神,两个歪七扭八的春字确实没眼看,但配着被冷风吹得摇摇晃晃的灯笼,也别有番生动活泼。她走过去接过赵灵手里的春字,寻了大门上正中央的位置糊上去,完事后拍了拍手微微笑说:“我的笔锋尖锐,还真写不出这一笔盎然春意来,闻人姑娘文丑颜良,端正又不死板,哪就拿不出手了。”
文香被夸得脸红,当下踩着雪去向赵灵炫耀,赵灵翻了个白眼,“诓人的话你也信。”
两个丫头说着又打闹起来,惹得路过的人纷纷侧目。
燕云歌望着两枚春字,感慨一年将尽,自己竟毫无所成,心下戚戚地摇了摇头,想着正事要紧,便去了后院找血影。
这个时辰,血影在练武场教导孩子们打拳,说来也怪,血影容貌惊悚,却极得孩子们信任和喜爱。燕云歌来了几次,都见过孩子们缠着她让她再耍招式的情形,明明是冷若冰霜的人,打起拳来却虎虎生风,如不起眼的鱼眼珠子被人细心打磨,盘出一层熠熠光华来。
燕云歌看了半晌,直到血影让孩子们先休息一会。
“我瞧着孩子又多了几个,里头可有能用的?”
宅子里的孩子越来越多,有原先路上捡来的,有自迁府后被父母卖进来的,慢慢地从几个孩子到现在的二十几个。燕云歌将孩子划为三类,聪明伶俐的继续读书,等年纪到了就送去书院,科考后慢慢地安插在各个衙署里;资质平庸但刻苦坚韧的就跟着血影赵灵她们习武,以后为她和各地方互通有无;至于文不成武不就但性格圆滑的孩子,稍加打磨就可以往宫里送,再不济还能培养成管事放在宝丰行,总归是自己一手调教出来的放心些。
血影沉默了一会,才道:“至多自保,里头出不了将军。”
燕云歌也猜到了,面上不显失望,颔首说:“能自保也好,世道险阻,总有我们顾不上他们的时候。”
血影忽而停下脚步,想说什么,最终没有开口。
燕云歌领她去了书房,要谈的事情机密,她特意着文香和赵灵在周围看守。
话才起了头,血影想也没想的拒绝了。
“你可想清楚了?”燕云歌忍不住惊讶,“这可是杏林沈家的人情,不说银子丰厚,单凭沈家的医术,未必就不能治好你脸上的烧伤。”
血影还是拒绝。
燕云歌一脸意外,“我能否知道原因?”她从未想过血影会拒绝,毕竟她这么缺银子。
血影想了想,沙哑的嗓音缓慢地说:“昔日旧主,不可。”
燕云歌愣了半晌。
昔日旧主?血影以前的主子是叶家的人?
是叶知秋!
那季幽……
燕云歌连忙喝了几口茶水压惊,模糊的记忆这会一点点清晰起来。出走江南前,季幽确实提过会有杀手一事,她当时因为柳毅之的纠缠身心俱疲,现在想来,季幽突然有此一问已很是古怪。
燕云歌看看血影,想问清楚又记起曾经承诺过不追问她的过往,忍住了冲动,挥了挥手示意她可以回去。
血影走后,赵灵跟着进来,心直口快地说:“老大,不如我去劝劝血影,这现成的御医可比我那师傅靠谱多了。”
燕云歌不想节外生枝,赶紧叫住了她,“她有自己的考量,我不能贸然坏了她的规矩。”
赵灵摸摸鼻子,也是,血影的态度至少表明了以后也不会与她们为敌。
比起血影的拒绝,燕云歌更在意季幽为何要隐瞒下杀手出自叶家一事?她拿季幽当知心朋友看待,季幽却因为一个男人对她有所保留。她一直记恨无尘的背叛,因此眼里容不得沙子,可那人是季幽,几度与她出生入死。
燕云歌一时没有决断,转去看赵灵,赵灵表情茫然,反对她眨了眨眼。
燕云歌揉了揉眉心,外头张妈进来回话道:“大小姐,秋家那边派人来问了几回,您看是不是要回去?”
赵灵瞪圆眼珠子,“老大你回去过年了,我们这怎么办?孩子们还盼着和你一起写春联,想初一集体给你磕头。”
燕云歌哑然失笑,“我又不是什么老祖宗,不兴这套。”又对张妈说,“我不耐烦应付宅院里的事情,张嬷嬷随我一道回去罢。”
张妈“哎”了一声。
两人才迈向大门,燕云歌就对着里头两排光秃秃的桂树皱眉起来。
她理想的宅院是盈郁羞竹,曲水流觞,最好是一步一景,又契合五行。可眼前这座府邸,原先布局就附庸风雅,加之文香一通乱改后,更是不知所谓。
心情好的时候不觉得,如今诸事不顺,她瞧着这个布局更堵的慌,便对张妈说:“开了春,你命人往后院种些榉树,前桂后榉,取个好意头。”
张妈连什么是榉树都不知道,寻思着和老槐树也差不多,嘴上只管应下了。
两人到将军府时,木童早在大门口等了一会。
“少夫人,您可回来了。”木童那表情跟见着死去的亲娘一样惊喜,领着人赶紧往里走,“您快去祠堂看看少爷,老太爷发了疯的训他,少爷身上就要没好肉了。”
“府中出了何事?”
木童赶紧说了前两天的事。
那日,秋老将军把秋玉恒叫去书房训了一顿后,秋夫人便拨了一些年轻貌美的丫头去书房端茶递水,用意也很简单,就指望秋玉恒会瞧上哪个,到时候开了脸就放他屋里伺候。
其中有个丫鬟心思灵活胆子大,趁着送夜宵时,一声不吭地解开了衣裳要自荐枕席,秋玉恒一时不察,被她撞了个满怀。这一幕恰巧被秋夫人撞见,当下说什么都要给这个丫头做主,要抬她做妾。
张妈听得满脸不忿,习惯性的想要为主子出头,突然福灵心至地看了燕云歌一眼,立即被冷眉冷眼的小主子震慑住了,暗叹夫人当年要有这气魄,那对母子如何能进得了门。
燕云歌站住脚,微微侧脸,“你与母亲说,此事我答应。”
“大小姐!”张妈失声喊她,木童更是傻眼。
燕云歌的表情没什么波澜,语气平静地像在谈天说地,“到底也是有了肌肤之亲,给个名分不为过。”
木童吓得直接跪下了,咚咚两声磕头,“少夫人,这话奴才不敢传。”
要让少爷知道他努力把少夫人叫回来,最后还同意给他塞丫头,少爷会气得打死他的。
燕云歌闭了闭眼,“我自己去与母亲说。”貂皮大氅一展,未走出两步,就被一双手拉住。
“少夫人,奴才求您先去看看少爷,少爷被关在祠堂一天了,你就是要做什么决定,也求你先去看了少爷再做。”木童攥着黑色大氅的一角不敢放,哀求着。
燕云歌皱眉,“他不会高兴你为他这么做。”以秋玉恒的骄傲与自负,是不会希望自己的奴才去帮他乞讨感情。
木童听出来有转机,将头磕地更响,“奴才知道,可是奴才心疼少爷,只要少爷能好,让奴才做什么都愿意。”
秋玉恒福气不错。燕云歌冷眼看着,又看了张妈一眼,张妈的表情有些古怪,欲言又止了半晌,才叹气说:“这种心眼多的丫头万万留不得,可就怕她是按着秋夫人的意思办事。”
秋夫人哪是要给儿子塞丫头,分明是借着丫头敲打大小姐。
燕云歌淡淡说了声,“我明白。”她又看木童,“你先去祠堂,我换身衣服就过去。”
木童额头磕地破皮发红,结结巴巴地问:“少夫人,你会去的吧?”
燕云歌无语了一瞬,转身就走了。
张妈还从没见过这么实心眼的孩子,将人拉起来,又问了几句详情,当得知那名丫鬟是春兰时,一张老脸瞬间绷不住了。
燕云歌今日难得休沐,着装上自是以自在为主,未想赶上秋家这一茬,只好勉为其难回房换了青色的裙装,改了一个简简单单的发髻,连个像样的发簪都没有,她干干净净地出现在书房时,让头痛了一天的秋夫人还以为是眼花了。
“母亲。”燕云歌简单地问礼。
秋夫人的表情有些冷淡,“何时回来的?”
燕云歌平静对她说:“才回来不久。”
秋玉恒那边再急,老太爷总不会打死他,可这位夫人已经对她愈发不满,尤其此次风波的由头还是燕相府出身的春兰,于情于理她都得先来见秋夫人一面。
秋夫人脸色不善,低头看着桌上的书册,翻了几页又借着喝茶的功夫仔细打量起这位媳妇。
她不是苛刻的主母,先前也是打心底喜欢这位儿媳妇,可自恒儿喜欢上她,这府里鸡飞狗跳的,哪还有安生可言。
到底是规矩立的太少,让她爬到恒儿头上。
秋夫人静了半晌,心里怎么想怎么不是滋味。
一个有心摆架子磋磨,一个耐心极好地面不改色,博弈下来到底还是秋夫人坐不住了。
“这几日庄子和铺子里的管事陆续要来交账,我原是想自己再管两年,让你们小两口安心地开枝散叶,但年关又要扫岁又要置办,我实在是分身乏术。一一,我知道你心里是有主意的人,此刻我便先问一问你,这府里的中馈你可愿意管起来?”
燕云歌心里意外至极,真掌管了中馈,她以后还如何脱身?面上仍是笑着回:“母亲说哪里话,能为您分忧,我高兴还来不及。”
秋夫人脸色稍缓,“对账不是小事,接手了就不能撂下,你可想清楚了?”
“在家时,这掌家一事先母也是教过的。当然,若遇到棘手的人事我会来请示母亲。”
秋夫人挑不出刺来,便将自己手上看的账册递去给她,“你先看看这本。”
燕云歌接过来,一目十行地扫了几眼。这是上个月的帐册,以红记出、以墨记入,记录了府中的每一笔进账与开支,大到铺子的收益、田地的租赁,小到每个人的例钱,买菜的明细,条目清晰,字迹工整。
她看到最后几页,是月底的结余,心算下来,分毫不差。
便合起账簿,对秋夫人道:“数额都对,没什么不妥。”
这才看了多久就说没问题。秋夫人心头存疑,却微笑着把另外一沓账簿都推给她:“那这些你带回去仔细看一遍,不急着要,你看完了再让人送回来。”
燕云歌便去抱过来一些,两人又说了几句闲话,她才告辞转身,倒是秋夫人将人叫住,“你回来可曾见过恒儿?”
“不曾。”
秋夫人突然冷笑说:“那便随我去一趟,我这不孝子昨儿说自愿从族里除名,哪怕是一身布衣,也好过留在将军府里给我们摆布。”
燕云歌露出诧异的神情,出去时对上张妈询问的眼神,微微一摇头。
秋老爷子许久没有动过怒了,而今朝野上下能将他气得捂住心口的,也唯有这个不成器的孙儿。他看一眼进来的燕云歌,又看一眼分明痛到抽搐还死撑的孙子,摆了摆手,“不必多礼了。”
秋玉恒褪着裤子趴在方凳上,刚挨了十下家法的他哆哆嗦嗦地抖得跟落叶一样,确如木童说的那样,屁股上没块好肉了。
两个执行家法的婆子一点没留情,杖杖见血,血肉模糊。秋夫人心疼地直掉眼泪,气这小祖宗什么胡话都敢说,万幸把老爷瞒住了,让他知晓哪是杖刑十下这么容易。
秋老爷子坐在上堂,沉声说:“现可知错?”
“我没错……”秋玉恒脸上冷汗涔涔,倔强地咬着牙回了句:“不孝子孙……秋玉恒谢祖宗家法教诲……”
眼见着老爷子怒沉下脸,燕云歌幽幽地叹了一声,一撩裙摆笔直地跪在方凳旁,正色说:“爷爷,能否听我一言?”
秋玉恒听到她的声音浑身颤抖,下意识抿紧唇,他不敢回头,怕看见她失望的神色。忍着忍着,到头来,还是呜咽一声哭了出来。
他这放声一哭,燕云歌肚子的话反而不好往下说了。秋夫人记挂着儿子的身体,可抬头看秋老爷子的神色并未心软,一时又慌又急,忙给燕云歌使眼色,希望她能给求个情。
秋老将军只叹慈母多败儿,孙子眼见要弱冠了还跟孩子一样,以后如何担得起振兴将军府门楣的重责,他再看燕云歌从容的起身,感慨四十余岁的妇人不如一个女娃稳重。
秋玉恒哭了一阵,气息渐弱,脸色也越来越白。
一个婆子上去查看,这才发觉他底下穿着的白色小衣皆是血渍,大叫不好:“不好了,少爷晕过去了!”
秋夫人见状,急忙转头对婆子厉声叫道:“还不去请大夫,不定是伤到根本了。”
底下的人面面相觑,瞧着老太爷愈发阴郁的神色,一时没个主意。
秋夫人只好转身对秋老将军,哭着说:“恒儿自然是该打,可太爷也请看在我们夫妻这些年膝下只有这个孽障,就此饶他一回罢,妾身保证从今往后对他严加教导,如有再犯,绝不宽宥!”
秋老将军面色泛冷,这小兔崽子连除籍这样的话都说出来,他犹嫌打轻了,可这孙子素来娇惯,难保婆子手下没个分寸真给打伤了,便缓了脸色,同意让他们安置去。
秋夫人忙擦去眼泪,让两个婆子担来床板,将秋玉恒先抬去里屋休息,自己也跟着一路走了。
偌大祠堂瞬间走了一半人,秋老爷子操心了两天,这会疲态尽现,旁边有茶盏递来,他抬头看了眼,是从头到尾只说了一句话的孙媳妇,皱眉说:“你刚才也想替这混小子求情?”
燕云歌笑了一声,又替老爷子添茶,“爷爷在玉恒身上用了心,可真将人打坏了,回头又心疼不过来,我便是要劝也是劝爷爷保重身子,何苦与那混不吝的置气。”
秋老爷子这才脸色好看些,说道:“他素日顽劣不知上进,你母亲不多加劝阻,还使劲想令他沉溺女色,却不知姨娘妾侍都是惹祸之胎,世家大族要想繁荣昌盛,除了男子要发奋上进,当家主母哪个不是有魄力和远见,哪个府里头不是干干净净!亏你母亲还是平伯侯府出身,竟想不通这点!如今孩子纵容坏了,都到这步田地她还来解劝,那混账不将祖宗门楣放在心上,轻易说出这等诛心之语,我若再不加以掰正,等到他明日出去不持身份的惹祸,万一打死人,她的哭哭啼啼到时候又有何用!”说到后头,难免又动了气。
燕云歌敬佩老爷子心思剔透,然而秋夫人囿于后宅,一心相夫教子,远见自然有限,她幽幽而叹道:“父母之爱子,则为之计深远,这不知事也有不知事的好处。”
这一句不知事说得自然是秋夫人。
秋家如今势微,盛京的人看在秋老爷子面上,叫秋玉恒一句小世子,可等秋老爷子百年后呢?秋夫人不盯着秋玉恒上进,反是盯着她的肚皮,恨不得三年蹦出两来,也不想想儿子还不上进,真有了孙子从小耳濡目染之下,又能长成什么好苗子。
不少女人以为生了孩子,夫君就能收心,不少婆母总以为儿子有了孩子,就会一夜之间成熟,成熟的本质无非是被巨大的压力推着向前走,运气好的能想明白自己的责任迅速成长,承受力不强的,反会因为后继有人,破罐子破摔去也。
女人总是为难女人,燕云歌总渴望飞到更广阔的天地中去,也是因为这个缘故。
这话说得十分大胆放肆了。秋老爷子皱眉,少有的认真地看她,女子的面庞不沾任何脂粉,头发随意绑了一个发髻,便是身上的裙装也是匆忙换上的,不难看出她对着装的心不在焉,或者是她对秋家少夫人这个身份的心不在焉。
他是老了,但耳不聋眼不瞎,有些事情选择睁只眼闭只眼,不过是怕逼得太过,适得其反。
可如今孙子不争气,也和孙媳妇不上心有关,秋老爷子想了又想,明白一切要徐徐图之,叹气之余推说自己乏了。
燕云歌起身告退,迈出门槛,身后有苍老又威严的声音传来。
“你在外头既这样用心,何不也在玉恒身上做做功夫,他固然不争气,但至少还听你的话。”
燕云歌愣了愣,站在门槛处回头一望,烛火下,昔年铁汉铮铮犹在,定睛一瞧又是英雄迟暮,她一时分不出老爷子的话是威胁还是恳求,又或是已经知道了什么,只好避重就轻地回道:“爷爷不必忧思过重,玉恒那边我会帮着母亲多劝劝他。”
人走了,秋老爷子垂下眼皮,满是失望。
秋玉恒皮娇肉嫩,又许久没挨过打,上了药后半夜突然发起烧,浑浑噩噩间又哭又闹的,一会说自己错了,一会说自己没错,把府里上下吓得整宿地没敢合眼。
秋夫人眼神跟刀子一样的在燕云歌身上打转,气她先前没有帮着说好话,燕云歌面不改色的批阅账本,连个眼神都没分给她。
秋夫人熬不住疲乏,最后留下木童小心伺候,等秋夫人一走,燕云歌干脆连张妈都打发去休息。她一手捧着账册,一手拨起算盘,不时用朱笔批改一二,不肖一个时辰桌上十几本账册已经消去一半。
木童左右无事,还帮着研磨、润笔。
“少夫人,您这字写的真好,一点都看不出是左手写出来的。”他惊叹道。
他跟着少爷读书,自然也识不少字,他敢说府里除了老太爷,没人能比少夫人写的更好了。
“这字算什么好,工整罢了。”燕云歌右手一拨算珠,头也没抬地回。
木童打了个哈欠,正想赔罪,就听到冷漠的声音回他,“困了就先去睡,少爷有我看着,不会出事的。”
木童赶紧拍拍脸,打起精神说:“奴才不困。”
“随你。”燕云歌合上账册,搁置一旁,木童眼疾手快,赶紧递过去一本新的,暗想少夫人这对账速度也太快了,这可是庄子上一年的账呀。
他整理的时候,偷偷打开已经对完的账册一看,彻底傻眼了。
字迹苍劲,批注详尽,连哪年哪月哪一石米记错了都给圈出来了,这读过书的就是不一样。
木童突然想起以前少爷还嫌弃过少夫人目不识丁,可现下一看,少夫人往日分明是藏拙。木童往深处想一想,只觉得还是老太爷高明,给少爷安排了门好亲事。
转眼到了全国封笔,燕云歌已在秋家待了三天。
秋玉恒自第二天转醒,一直将自己头闷在杯子里不说话。上药、喂食、出恭,都是木童在旁伺候,他甚至连燕云歌的面都不见,一看见她过来就将头扭过去。
木童唯恐她会生气,寻了在外头的机会,偷偷说:“少爷从未在这么多人面前丢面子,怕是有些不好意思面对少夫人。”
燕云歌的脚步蓦然停住,冷眼看向里间床榻上的背影,淡淡地说道:“他多虑了,我和个孩子置什么气。”
她的声音不轻,木童僵在那里,看着清冷的背影远去,心里祈祷少爷没有听见。
屋子里,秋玉恒心里涩涩发疼,比起被她漠视,最难过的还是被她看不起。
可前尘种种,都是他咎由自取。他口不择言,脱口说出不要当秋家人,宁愿做个平头百姓也好过整日被父母拿在手里,他不想纳妾,不想读书,也不喜欢上进,他就想守着她这么安安稳稳过一辈子哪里不好了,可是谁都在逼他,爷爷让他上进,母亲不喜欢娘子了也不让他喜欢,军器署他又得不到重用,谁都对他失望,又必须对他抱有希望,他不喜欢这样,很不喜欢……
如今连她都当自己是个孩子,她也和母亲没两样,当他是负担……
“少爷……”木童跑过来想说些安慰的话,但又不知从何说起。秋玉恒默默抹了眼泪,说了句:“我没事,你出去吧。”可半夜里他还是发起了高烧,额头烫手,身上却冷得发抖,哆哆嗦嗦地跟掉入冰窖一样,一直梦呓不断。
秋夫人吓得没了魂,赶紧把守在府里的大夫叫进来。
大夫摸了摸秋玉恒的脉象,又翻开他紧闭的眼皮看了看,面色凝重地拿出一筒鹿皮卷,在秋玉恒几处穴位施了针。
人没有醒。
“恒儿究竟如何了?”
秋鹤也已赶来,大夫收了针,冲几人摇头道:“小世子忧思过重,怕是在梦里被什么拖住了,现下又发着热,身子虚弱,老夫不敢开药,晚点再为世子施一次针,如若再没有醒,还请秋大人另请高明,切莫耽误了小世子的病情。”
秋夫人慌地六神无主,站都要站不住了。
秋鹤镇定许多,赶忙请大夫借一步说话,大夫婉拒了银两,叹气说:“秋大人,医者仁心,老夫断不会能救而不救,您若有法子,趁今日宫门落钥前去太医院看看,兴许还有哪位太医坐职,老夫才疏学浅不敢误了小世子的病情。”
大夫说得十分诚恳,秋鹤感激不尽,给了丰厚的诊金,至于太医院那,他并未有相熟的太医,想到燕相与宫闱中人一向交好,忧思之下决定亲自去一趟燕相府。
“父亲。”
游廊下,一直冷眼旁观的人从黑暗中走出,秋鹤皱眉地看着这位冷清的儿媳妇,面色不善道:“我有急事要出去一趟,你有什么话等我回来再说。”
“与其惊动太医,父亲不如听一听我的主意。”
“你……”
半个时辰后,两道身影扣响了夜幕中的将军府大门。
门人打开门,只见其中一道身影客气地拱手,“在下沈沉璧,听闻秋世子身体有疾,现携家兄来给秋世子看诊。”
更哆文章就捯ΧяòǔЯòǔЩЦっ℃òм
第197章染疾
同类推荐:
偷奸御妹(高h)、
万人嫌摆烂后成了钓系美人、
肉文女主养成日志[快穿系统NPH]、
娇宠无边(高h父女)、
色情神豪系统让我养男人、
彩虹的尽头(西幻 1V1)、
温柔大美人的佛系快穿、
师傅不要啊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