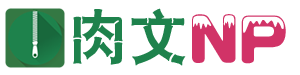蒹葭_高h 作者:八爪南宫
雍合殿的一场交锋在皇帝还没有踏出殿门的时候,就被快马加鞭送到了竹殿,依沉络口谕跪在地上的江采衣倏然抬起头,望向竹殿幽幽延伸出去的阴绿小径。
草木带著湿气,烟柳画桥,风帘翠幕,膝下的冰凉触感一直渗到了骨头裡,眼睛裡湿润寒凉。
皇上他,居然付出了那么多代价。
江采衣只觉得手指连握起来的气力都没有,双手趴在冰凉的于是地砖上,降低了身体缓缓将额头抵在地上,任凭一旁的嘉宁怎么叫唤,也不起身。
心头裡泛起的感觉除了苦涩还是苦涩,堆在胸臆间,是让人哭喊不出来,搅得五脏六腑难受的酸楚。
她其实不太懂得朝堂上的风起云涌,但她知道,以慕容家的胃口,能够如此乾淨俐落的放了她,其代价绝对值得让皇上的头疼上一疼。
终究,终究,她让他付出了这样的代价。
她这样一个居心叵测,为了复仇而来到他身边的女人,在他怀中汲取了那样多的温暖之后,又给他带来了那样多的麻烦。
这是头一次,江采衣产生了退缩的念头。
一刹那她不想复仇,就算江采茗死,就算宋依颜死,她的妹妹,她的母亲,也都不可能从幽冥之地回到她的身边。
如果这样,如果这样,她还要为他添这些麻烦么?
这样想著,身体就一层一层的冷下去。
眼前的光影朦胧起来,竹叶上反射的日光凉津津的,足下初生的青草萌生出一点绿意,浅浅的足履声传来,草地上的露珠摇滚而落,有种缠绵柔和的银色。
陛下回来了,衣角犹然带著微微的血气,周福全招呼著众人张罗沐浴,另一队宫人则捧著锺鼎鱼贯而入竹殿,饭食的香气弥散在空气裡。
茫然间,江采衣模模糊糊听到周福全凑过来小声交代,“娘娘,皇上一听御花园出事儿,拔脚就赶去雍合殿了,直到这会儿连膳都还没用过,娘娘心疼心疼皇上,快去服侍皇上用膳吧。”
说罢居然在她手裡塞了一双筷子。
江采衣有些无措的看著手裡的文犀乌金筷,她还跪在地上,皇帝已经进殿去了,这……
她咬著嘴巴,以跪地的姿势微微抬起头看去,沉络站在九枝梅花黄梨桌前,几个宫人围在帝王身边替他更衣。
宫女们彩袖殷勤,素手玉锺之间柔软轻折的来回。
一件一件的佩饰和外衫递上去,一件一件的旧衣换下来,清凉的竹骨撑上挂著云雾白的蝉翼纱,竹殿裡映著朦胧清冽的绿,皆似化在春水中一般,远处太液池烟波纵横,连光线都透亮起来。
“过来。”沉络挥退了服侍的宫人,嘴裡咬著一根极细的素色犀角琥珀发梳,长长的头发散散挽在肩头,从素锦纹路上轻缓流泻,最终用发梳别过固定住。
江采衣起身,拿著筷子起身走至桌前,然后又低头跪了下去,触目间是他衣袍的下摆。
他穿著常服,不同于正冠袍服的豔丽,仅仅是在衣袍一角绘著婉转苍劲的花影暗纹,衣是素色,花是素色,只有发泽乌黑优雅,顺著他坐下的动作而轻轻搭了几络在椅上。
沉络抽走她手裡的筷子,定定放在桌上,“吃饭。”
江采衣粉唇蠕诺,声音比蚊蚋还低,“皇上……”
他眉角一挑,“先起来,吃饭。”
她有点像个犯了错误的孩子,手足无措的等在长辈面前,直到皇帝轻笑一声,亲手盛了一碗鲜笋碧丝汤放到她跟前,江采衣才忙不迭的低头拿著勺子去舀,可是半途才反应过来,怎么能让陛下给自己盛饭?手裡的勺子就砰地一声掉在了桌上。
乱七八糟,狼狈不堪。
沉络扶著额头差点就笑出声来,殷红的指尖插入耳侧柔顺的黑髮,三分无奈,三分怜爱的看著手边慌乱的少女。
“罢了,不说清楚,你怕是食不下嚥,朕也没法好好吃饭。”沉络淡淡的说,于是江采衣赶紧从椅子上挪下地,规规矩矩的重新跪在皇帝身前。
“跪的近一点。”他吩咐。
江采衣讷讷,挪动双膝,一直到她的鼻尖都碰到他的膝盖了,才堪堪停下。
沉络垂眸看著她,漆黑发线间缀著几枚珍珠银钉,一弯清瓷色泽的耳朵透出鬓髮,小小的柔软的仿佛风下低垂的芙蓉花苞一样柔嫩。
沉络微微顿了顿,才放柔声音她,“知道你错在哪裡了么?”
“臣妾大意被人陷害,给皇上添了许多麻烦,害的众位大人逼皇上……”眼眶热辣辣的,她几乎要说不下去,脑中就回忆起方才有人报来的消息────皇上赦免了那几个贪渎的死囚,还封了慕容云烈先锋将军!
指甲缩成拳头,刺进掌心的肉裡。
已经送出去的军权要如何收回?
已经赦免的死囚该如何重新收监?
他的霸业,他的天下,居然因为她这么一点事而将费如此周折!
发生事情不怪你,但事情发生之后呢?你就这么乖乖的被慕容千凤和叶子衿逼在雍合殿?朕平时是怎么教你的?”
“臣妾知道,臣妾知道……”江采衣嘴唇动了动,长跪倒地,连眼皮都不敢抬,“嘉甯已经带来陛下的剑,臣妾应该立刻奉杀所有人……”低低的声音含在嘴裡,低低一字一句艰涩吐出,她缓缓闭上睫毛,背脊都在轻轻颤动。
“说得对。但你做了什么?”
她做了什么?
她哪裡有脸回答?
嘉宁飞速取来了剑,她却眼睁睁看著一动不动,任凭消息扩散出宫,给足了慕容尚河和叶兆仑他们时间,一直等到尘埃落地,她都没有动过那柄剑一根指头。
江采衣张了张嘴,却发现自己半个字都说不出来,她盯著帝王膝上的暗纹花影,将脑袋深深埋进浓重的阴影裡。
“你有天子剑,六宫皆知,为什么叶子衿还敢犯险招惹你?采衣,你最大的问题,就是让叶子衿看透了你不会要她的命!被人看透了就一定会被人操纵,叶子衿也在赌博,这一场赌局,她赢了。”
“……”江采衣双唇微微翕动了一下,到底还是把涌到口边的话吞了下去。道理她懂得,没错,没错,那时候,她只要多一点胆识、多一点狠心,分明就可以把这场惊涛骇浪的事情举重若轻的压下去,就不会搞到皇上几乎和慕容家撕破脸谈交易的程度,可是,可是……
“朕把你揽在身边,是想让你坐哪个位子,你不会不知道!拿著天子剑还镇不住六宫,以后谁能服你?就算朕把你硬拉上后位,你也要能自己坐稳!”
“陛下……”
“懂么?!”他把筷子重重放在桌上,语调中骤然狠厉。
江采衣肩头狠狠震了一震,神色哀凉。
这裡面种种利害关系她当然明白。
他一声声训诫并不严厉,听不出喜怒,甚至不是指责,可是她还是想哭,在这个人的面前,永远那么那么软弱呵。
“……懂。”时间抽丝剥茧一样一丝一丝的剥落,许久,小小的涩哑声音才传来,不用力分辨就几乎无法听清。
沉络淡淡扯动红唇,看著身前跪坐著的姑娘缩的更小,几乎将自己要将自己埋进眼前的地缝中去,好像一隻北风中瑟缩抖颤的小雏鸟。
然后,他听到了她比方才更细弱十倍的声音。
“臣妾懂得,可是臣妾……做不到。”
做不到。
是的,她猜到,猜到害死楼清月的人约莫就是叶子衿,约莫也有慕容千凤一份儿,牵扯其中的人数也数不清。
她也清楚阴谋错乱间,必须快刀斩乱麻,将一切在事态爆发前了结乾淨。
可她做不到。
所有事,终究是一个“猜”。
她不能肯定凶手一定是叶子衿,也不能肯定就是慕容千凤。这世上终究没有靠“猜”十拿九稳的事情,那么,她又凭什么夺取她们的性命?
仅凭臆测么?
那样,她和宋依颜又有什么不一样,和夺取玉儿性命的那些人又有什么不一样?
她凭什么充当审判者,去裁决他人的性命?
玉儿幼年时,她曾经带著苍白乖巧的妹妹一同踏秋,玉儿身体不好,那是姐妹俩很少有的一同出游的美妙时光。
秋色那么纯粹,隔壁人家的低矮牆头伸出了一树小黄灯笼似的杏子,风吹的狠了,就落下一地。
江采衣至今还记得妹妹的手掌握在手裡,那种软糯的触感,那样温暖那样柔软,至今刻骨铭心。
玉儿曾经羡慕的说────姐姐,杏子看起来好甜,玉儿想吃。
邻家的夫人扭头,从杏树下瞥来幽凉的一眼。
姐妹俩也没有多做停留,就离开了。
然而第二天,那株杏树上金黄的杏子却渺然无踪,似乎一夜之间被人给摘了个乾乾淨淨,隔壁人家的夫人就找上了都司府,说玉儿偷摘了她家的杏子。
江烨当时十分生气,宋依颜给那夫人柔柔的赔了礼之后,就罚玉儿去扫一地雨水后湿积的落叶。
玉儿那么小,几乎是拖著巨大的扫帚,在薄薄的秋日裡清理一地落了三尺、黄红交杂的厚厚落叶。
秋天的早晨清冽如同初冬,已经有薄薄的碎冰凝结在砖石上,玉儿身体不好,动一动就要咳嗽。
她心疼的不知如何是好,却偶然在雪芍的房间发现了整整一篮子金黄的鲜杏,江采茗跟在宋依颜身后笑闹,偶尔也从袖口裡摸出一颗杏子吃。
她恨得嘴裡发苦,一把抢过玉儿手裡的扫帚就要衝去找宋依颜评理,却被玉儿的小手捉住,她的妹妹微笑著看她,眼睛裡有著蓝天白云最纯洁乾淨的神采。
“姐姐,”玉儿说,“不要去,她们的杏子或许也是巧合。”
“巧合?鬼才信那是巧合!”她的笑冷透,“宋依颜安了什么心我会不知道?她八成是故意的!”
“但她也或许是无意的。”玉儿歪著脑袋看她,“姐姐,因为我被冤枉,就要去冤枉别人么?”
“……”
小手扯了扯她的衣袖,玉儿将柔嫩的小脸埋进了她的怀裡,软软的一个小身子,塞满了她的手臂,“姐姐,玉儿被罚了也没甚么,可是玉儿不愿意姐姐做错事。”小小的孩子咕哝,“如果姐姐真的错了,你一定很难过很难过的,玉儿不要你难过。”
“可是……”她的嗓子好堵,心疼的摸著玉儿软绵绵的绒发,“可是你受罚,别人看著,都会以为你有宵小途径,偷人家的东西。”
“那又怎样呢?”玉儿就轻轻笑了,那样清朗,“我知道我没有!”
────我知道我没有!
既然问心无愧,又何须在意他人目光?
品性德行是自己的,又不是长在别人身上!
受罚又如何?被邻家夫人用异样的目光看著又如何?────我知道我没有!
她的玉儿,最乾淨的玉儿,最温柔的玉儿,水晶一样的玉儿。
玉儿的微笑她记得很清楚,黑曜石似的眼睛像晴天下的大海一样宽广阔达。
那是她的妹妹,留给她的最美好的回忆。
那是她的妹妹,留给她的最珍贵的东西。
是不是玉儿太美好太美好了,所以老天就要早早把她收走?
想起来,心口都是疼的,疼的几乎要断了呼吸。
所以,她做不到。
即使叶子衿和慕容千凤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就是真凶,她们毕竟还有百分之一的可能是无辜的,夺她们的命,她做不到。
吸了一口凉凉的气息,竹殿气息微凉,外面雨过天晴色照的一室青翠,风过树叶有著细微的漱漱琳琅声,雨水的气味还未完全消散。
沉络并不发怒,睫毛轻轻翕动,漆黑琉璃一般的眼睛垂下看来,衣袖下摆一朵泼墨似辗转妩媚的深白色合欢随著他的动作伸展妖娆。
眼前的姑娘,死死跪在地上,下巴紧紧缩著,却又隐隐有倔强执拗,眼睛裡含著的泪水在睫毛下隐匿,似闪非闪。
唇畔忽而失笑,沉络只觉得气也不是,笑也不是,训斥也不是,说理也不是。
道理她都明白,但真的让她改,怕非一日之功。
江山易改本性难移,罢了。
浅浅笑歎一声,他终究还是微微俯下身去,手指探入她因为流泪而湿润的颈侧,指腹温暖的绕到她后颈,温柔的抚摸,“起来吧。”
“可是,皇上……”江采衣声音裡有丝犹豫,这么大的事情,就这么过去了?
她还有好多事情要问他,还有好多感谢没有说。
她想问问他,现在后悔行不行?这条命不要了行不行?把你放出去的军权收回来行不行────
骤然,修长的手指抓住她的手臂,就势往上一拉,江采衣跪久了的膝盖酸麻,足下就绊了一绊,被他拦腰揽至膝上。
沉络双臂展开将她紧紧抱入怀中。
她的面容被藏入他颈侧温暖的,被黑髮覆盖的颈窝,有碎发在肌肤与头髮的界限之间细碎的垂了下来,“方才就想说这话……采衣,你受惊了。”
他偏过头,红唇柔软带笑,有著温暖的热度,触上了她后颈露出髮丝的肌肤,就低低吻了下去。
似有一条热热的线直逼进跳动的脉搏,江采衣没有躲,反倒是依偎的更深了一点,浑身轻轻发著抖,揪住他肩部的衣衫,呼吸著发间淡雅的海棠香气,颈子后面是他温柔的吮噬。
他的手臂很紧,向来抱得她有点痛。
可是,心底却是很欢喜很柔软,翻涌著滚热的甜蜜。
心裡念著他的名字,闭上了眼睛。
鼻尖深深的埋入了他的发间,脸颊磨蹭著帝王肩膀处银线疏疏绣的几枝毓秀花,心裡远远的仿佛就吹来了一点春意。
窗外是雨过天青色的竹林,湿湿的雾轻薄如烟,夏日的风吹进竹殿是阴凉中带著和暖的气息,屏风上的茜色碧纱微微鼓起。
“皇上……抱歉……”拥抱了许久,小小的,带著泪意的声音从沉络耳垂下传来,怀裡女子的吐息轻轻吹动了他颈侧的肌肤。对不起,让你如此为难。
莫名就更收紧了手臂,沉络眉眼轻动,傲慢的漆黑眉角斜挑,那瞬间,宫衣下摆随风欲起,竟然比满地盛放梨花更为繁盛清雅。
刹那间,几乎要为手臂间的柔软触感沉迷了一瞬。
“真觉得抱歉,以后就不要让朕担心成这样。”微带泪意的姑娘被他的手指捉起下颚,红唇笑歎,抵上去,含住了她带著泪光的眼睛。
石阶泛湿,云随光动,转雨横风疏,棉瓦陡峭。
整座宫室,绵延百里颜如玉,春花秋月遍地,国色天香充盈。
可是,在这一片接天连地的富丽金红色楼阙中,在倾国倾城的红粉佳人丛中,只有她一个,对他而言,是女人。
江采衣。
突然就想起来初见,银烛秋光冷画屏,朱砂点额心,碧波作裙,两重心字罗衣。
那时竟然无法想像,这样的一个女人抱在怀裡,连血液都是刻骨的疼。
服侍御膳的宫人被周福全喊走,偌大的竹殿裡似乎空了,又似乎满满的。
凉风嫋嫋泛崇光,香雾空蒙转宫阙,这时花正当春,人亦少年,都是最美好的时光。
风一来一回一个徘徊,水一流一顿一片清澈。
软云样兜著的青丝漆黑流瀑一样的坠下肩头,采衣的肌肤上泛起一丝一丝的细细战慄,她透过他黑髮的间隙看去,一曲添香的琼花衣袂成双,他衣袖上是一层一层,丰美华丽,燃烧一样的梨花。
“陛下……”她还想要再说几句什么话,就已经被深吻堵了回去。修长手指嵌入她指缝的间隙,狠狠一握,根根手指交缠,轻易就夺取了她所有心思。
道歉的话,放弃的话,就不要再说了。
世上最难是有一人温柔待之,其次温柔相待。
春光易虚度,不如早早相逢。
******
烟花满宫阙,柳絮任凭游,雨后的北周宫牆被雨水洗的鲜亮,远处春水初生,春林初盛,更添春风十裡。
山是青的,水是碧的,柳絮翻转,年华明媚。
人都被周福全叫走了,沉络也无意叫他们进来,江采衣挽起衣袖替君王布膳,杯盏碰撞间发出细微的丁玲声,就像是随意漫弹的琴声。
此刻还有残留的雨水顺著竹殿顶端粗大的空心翠竹挂落下来,星星点点像是还在飘著毛毛细雨一般,夹著一点清亮的银光。
江山如洗,只看见杏花梨花漫天尽飞散,顺著风吹进了清凉的殿门,风吹过带起馀凉裡混著淡淡花叶芬芳和竹叶酒清苦熏人的气味。大殿内静得恍若一池透明无波的秋水。
竹殿极为宽广,虽然不像其他宫阙那样极尽奢华富丽,却清淡优雅的自成风韵,为了君王住的舒心,竹殿内所有物事线条细柔,色泽清凉,大约主要以浅色为主,配出了空旷疏离的美感。
接著正寝殿一侧,是一座空旷的空透宫室,高高的弯起的瓦簷全用绿琉璃铸成,瓦片极为细碎,远远看去像是连缀的碧玉。
瓦片透明,仰头看去能够看到高阔的苍穹。
四周没有牆,只有四根粗大浅碧色的木柱撑在四角,几级台阶往下就是幽幽绿水,散著层层叠叠的落花,空静优雅。
用罢了膳,沉络左右也无事,著人席地就铺展开一袭洁白象牙席,凉悠悠贴著临水的地板,象牙席由薄如竹篦的扁平象牙条编织而成,津津的幽然温凉。
席上放著矮脚小几,几上加著小银吊子上,咕噜咕噜的滚著带著竹叶清雅气息的酒。
江采衣跪坐在矮几边,身侧的帝王则在另一边,半靠著青玉案几,有一盏没一盏地喝著温热的竹叶青酒。
帝王极为漆黑长髮沿著衣袍的褶子蜿蜒顺流而下,流水散落的黑色芙蓉般,只挽了一根最简单的芙蓉簪。
清雅白衣,素淨到了极致,偏偏面容又因为酒意而带起薄薄绯色,豔丽到了极致,春风软醉,倾倒河山,是她没有见过的随意姿态。
“皇上,先锋将军就这样给出去,要收回来可就难了。”江采衣看他那般悠閒,似乎将先前雍合殿一番腥风血雨全然不放在心上一般,不禁忧心忡忡的扯了扯他的衣袖。
“没想到,你有一天也敢和朕谈论朝政的事。”沉络嗤笑。
后宫不得干政的戒律江采衣一直十分遵守,但这一次,她显然是愧疚的狠了,才对这件事念念不忘。
指尖轻捏银白点朱的流霞花盏,他笑意淡泊如明月下疏离的花枝,“采衣,真正的权利是夺不走的,朕能给的出去,就能收得回来,军权也一样。何况,你真的以为北伐的先锋将军好当么?”
“怎么不好当?”她问。
竹叶青酒并不烈,甘甜而绵长,沉络唇瓣浅浅抵著酒盏,含笑举杯,以袖掩面,饮了一杯,“你可知道,瓦刺人馀部此刻聚集在什么地方?”
江采衣略一思索,勉强搜刮了些许看邸报时馀留的记忆,“在狼突江以北……吧?”
“狼突江在哪裡?”
这就问倒江采衣了,她没有看过地图,怎么也想不出来,沉络也不为难她,只是指尖在虚空中略略一点,似乎是画了一个江水奔流的姿势,“狼突江接著北海,低转入盆地,倒灌入胭脂山脉。”
北海,低转,倒灌……江采衣猛然“啊!”了一声。
“想到了?”沉络把玩掌中玉杯,轻轻哂笑,“海水倒灌入江,狼突江水含的全是盐,寒冬腊月也不会封冻。北伐军中并无水军,慕容云烈连江都过不去,怎么打?”
江采衣嗔目结舌,沉络的手指越过矮几,给她倾倒了一小盏清清的酒。
“你以为朕真的要打瓦刺?”他嗤笑,“区区瓦刺,朕根本不放在眼裡。朕放出军权,是要收回掌握在世族们手中的另一项权利,那是他们的安身立命之本。”
江采衣犹疑的踟蹰许久,“皇上说的是……财权?”
沉络摇头,“不甚准确。采衣,北伐之后,就见真章。”
江采衣怔了一会儿,小小的玛瑙酒盏捧在手心裡,又硬又沉,镶金兽首玛瑙杯纹理极细腻,酱红地夹橙黄乳白,浓淡相宜,晶莹鲜润。
一丝疑虑滑过,拿在手上的杯盏登时觉得滑腻的捉不住。
“皇上,狼突江或许真的很难渡过,可……慕容大人就想不到这一点么?”
慕容尚河难道不会想别的法子?老老实实驻军铺桥,或者绕道……这世上,本就没有过不去的天堑!
“他自然知道,所以他一定会屯军狼突江外。”沉络朗声大笑,“数万军马要过河,造桥非一日之功,而瓦刺人为了活命,断不会给慕容云烈铺桥的机会。所以,慕容云烈最终的选择一定是绕道。”
“绕道……”采衣将这两个字反复念了几遍,却还是觉察不出来个所以然,但是握著杯子,看著沉络情适宜的模样,她觉得心突然就定了。
他是称霸天下的雄主。旭阳关外曾经战火屠戮,有了他,三百里平坦,至今百姓无忧。
或许没有什么事情,是这个人不能掌握的。
水动风凉夏日长,长日夏凉风动水,凉风动水碧荷香。远处桃花自悠然,几重烟雨渡青水,轻红醉洛川。
美貌的天子仰面伸手,笑意似轻轻的一朵桃花浮现,压一压被风吹起的柔软发梢, “本朝自太祖之初,说过一句让朕厌恶至今的话────帝与世族共治天下。天下,岂是可以共治的?江山如卧榻,岂容他人鼾睡?北伐军撕开了口子,慕容尚河想要染指就染罢,哪家想来都可以。待朕得到了想要的东西,就毕其功于一役。那时,慕容……”
慕容,你打算怎么死?
薄薄的笑意滑过舌尖,仿佛贴著锋锐的凛冽气息,沉络笑吟吟的弯起漆黑柔软的美目,和同样柔软的唇。
隔著矮几抓过江采衣密密搂进怀裡,他的笑意贴著她白皙的脖颈轻颤,“来,采衣,如此趣事,当浮三大白。”
******
“唉!”采衣小小惊叫一声,腰就被他的手臂给箍紧了。竹叶青酒的味道传来,清瓷硬而冷的边缘就触到了她的唇瓣,带著凉意微微启开饱满的粉唇。
竹叶青酒是用烹天泉水酿之,香韵尤绝,暖暖的一阵微醺的暖意就弥漫上来,沉络一手撑在地上,侧头吻她的鬓髮。
唇齿贴在肌肤上的感觉酥而清柔,让人的心底都微微快乐蜷缩起来,甜而朦胧,像忘却了的忧愁。
“皇上,臣妾不是很会喝酒……”脸颊骤然就一红,他的衣衫随意,敞落间依然散开些许,看得她难为情的左右撇著眼珠,躲开他襟口的一段极豔的肤光。
“无妨。”他无意勉强,白皙的手指握在莹透的酒盏上,红唇似笑非笑抵在杯沿,莫名妖豔的令人心头发颤,“卿且随意,朕自倾怀。”
台阶前的绿水被残留的雨珠打出圈圈涟漪,仿佛漫然随意的琴声,他揽著她,慢慢自斟自饮。
于是落花浮水上,于是牙席凉生温。
繁花似锦觅安宁,淡云流水度此生。
******
幽静之中,骤然就听到骏马嘶鸣声。
禁宫之内向来不能走马,怎么会有马匹奔跑的声响?
江采衣支起身子看去,周福全撩开层层叠通往内殿的白色通纱。有漆黑色的骏马恍若流电,从狭窄的蓝田玉砖回廊踏步而来,如行冰上,发出急骤而清脆的声响。
一转眼,漆黑的骏马就已经停至眼前,马蹄踏上凉悠悠的竹木地板,震得一汪绿水都悠悠晃荡。
江采衣转头去看沉络,“皇上,这是……?”
沉络放下手裡的酒盏,“今日是你的生辰,朕要带你出宫,忘了?”说罢起身走下台阶,伸手轻轻在骏马光滑油黑的颈边轻轻抚触。
骏马亲昵的弯过脖子,用柔软漆黑的鬃毛磨蹭著主人修长有力的手,沉络拢了拢襟口,随手取了一支琥珀犀角簪挽了长髮,纵身翻上马背。
天子一身浅白衣衫,流飘若云,偏偏发是乌黑,唇豔如脂,似立于比水墨还更清淡的画间,骤然绽出无边无际的豔丽牡丹,几乎要灼伤人眼的绝顶风姿。
沉络一手扯住骏马躁动的缰绳,微扬嘴角,“采衣,寻个时候,学学骑马罢。”
江采衣看著那一个手掌都包不住的巨大马蹄,顿时产生了一丝不详的预感,身子就往马蹄外的范围躲了躲,“什、什么时候?”
美貌的天子大笑,一个弯身就把她捞上了马背,“现在!”
还未来得及发出惊叫,周围的景物就如同雷火一般狂肆的褪去,绿色、蓝色、红色,夏日的潮湿水汽竟然仿佛海浪一样批头浇了过来!
沉络纵身策马,踏过一池浅浅的池水,踢散了无数莲花,踏过宫侍密集的庭院,惹来一串惊叫!
“陛下,陛下慢点!你,你这是要去哪裡!”江采衣忍不住捂住眼睛尖叫出声!
她只是个普通的姑娘,从没摸过骏马,更没有用这样的速度驰骋过!
人人四散躲避,景物扭曲惊转,他操控的速度太惊人,每每让她以为自己下一秒就要连人带马撞碎在前方的障碍物上!
内宫虽然宽敞,可是宫阙回廊扭曲转折,太液池上的白玉桥搭在清波浩渺之上,他就这么带著她风驰电掣,几乎用上了千里奔袭的疯狂速度!
内宫策马不比在平原,极难极险,何况皇帝马背上还带了一个人!
在宫牆裡使用这样的速度一个不小心就是粉身碎骨,几个急转弯处马身剧烈倾斜,江采衣只觉得脸颊擦著宫牆飞驰而过。
她紧紧闭上眼睛死死抱住沉络的腰,每每以为下一刻就要连人带马飘翻到在地上!
众目睽睽之下,天子带著宠妃风驰雷电般直冲宫门,瞬间就闪电似的掠出禁宫。
呼呼的风声在耳边迅疾刮过,在内宫惊险万分的驰骋许久,采衣似乎猛然感到身上一轻,骏马宾士的速度越发快了,足下却似乎开始平坦宽展。
“睁开眼睛罢,已经出宫了。”沉络轻笑,微微压低了胸腹,清凉青丝拂上她的脸颊,微微睁开紧闭的双眸,然后入目的是,人间一片繁华。
萤火8
同类推荐:
【快穿】欢迎来到欲望世界、
爱欲如潮(1v1H)、
她的腰(死对头高h)、
窑子开张了、
草莓印、
辣妻束手就擒、
情色人间(脑洞向,粗口肉短篇)、
人类消失之后(nph人外)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