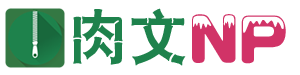这说的实在是很煞风景。虽然做出这种举动,也不是自己的初衷,何况这天的晚风,这么寒冷,光是用脚尖碰到水面,都凉如针刺,可事情到这一步,已经停不下来了。
自己近乎疯狂地往水里扑去,御川水浸到大腿,浑身直打哆嗦。其实根本不应该是这样的。可表演的欲望一点被点燃,无论如何都停止不了。藤大纳言从未想过要真的找回哥哥的面具。何况要从何找起?一想到哥哥在人前出丑的种种,掺杂方才被众人所指的委屈。自己的眼泪都快要掉下来了。
分明不是自己受了屈辱,却比自己受了屈辱更甚。就算毫不受辱,只要呆在人前,自找麻烦的心思就会油然而生。以前强装委屈,或自讨苦吃,是为了博得家人的爱,现在是为了什么呢?
岸上的陛下,对藤大纳言大呼小叫,作势要跟着下水。侍候的藏人也只是将陛下拉着,对藤大纳言歉意地笑笑。去寻找不可能被寻找到的面具,还是当下的滑稽表演,带来的无非是绝望。越是觉得绝望,越是表现得疯狂。干脆躺在这水里也无妨吧。而且仔细想想,还有谁能得到允许下到御川里的特许?恐怕世间也唯己一人。得到这种驱使而前进的双脚,忽然间碰到了一个很光滑的东西。
藤大纳言心里咚咚地跳着,伸手往水里一探,哥哥的面具被老老实实地抓在手里。本来不指望找到的东西,一下子找到了,心里反而不一定会高兴。
从水里走上来,任风吹着,比在水里还要寒冷,拿着面具的自己,不断地打着颤。连自己的前驱也找到这里来了,大声问道,“怎么弄成这个样子?就算是对式部大辅也不好交代。”
朱雀帝攥自己的手问,“不喂了吗?”
藤大纳言的双脚离开水不久,就变得像恶鬼那般通红,仔细地看,那脚趾也长得很奇怪。别人大都是五根指头都很匀称,就算不慎在外人面前露了出来,也能当做美丽的风景给人家收获。而自己却生长着一根颇为粗壮,甚至可以说是诡异的二趾,较大脚趾长出一大截。因为一度能够见到的赤足也只有自己的,从前还以为人人的脚趾都生来这样。
现在这双脚变成了红色,愈发显得怪异,真的好像恶鬼的双足立在地上。衣服上的水滴滴答答地往下淌。以自己为中心的这一小块地方好像正在下雨。
本来还想佯装没有事的样子,对陛下说些玩笑话。可自己的眼泪一下夺眶而出,嘴上难以抑制地说道,“我想回家。”
哥哥在毁容以前有写日记的习惯,凡是家里事都要掺一脚的自己,也亦步亦趋地弄了一卷写日记的纸。其实自己根本没有写作的心思,大多时候,也只是在上面涂涂画画,要么就是写一些口无遮拦的牢骚。那时女房间有一种将时下鲜花收集起来夹在书信的流行。藤大纳言也就学着她们的样子,把小石子,蚂蚁的尸体,或者竹叶也放到纸张的夹层里去,母亲的一个女房就对自己大声说,“这样是不可行的!”还把自己收集的宝物信手抖落到院子里,晚上的时候,自己看见这个女人从自己的日记里偷纸。
藤大纳言背后将她喊作忠赖夫人[7],不慎被人听到了,竟咯咯笑着,也跟着这样叫。后来到底觉得是很不好的话,久而久之,将那个女房做的事遗忘在脑后。
千辛万苦地回到家里,哥哥也没有回来的迹象,藤大纳言给自己换了一套衣服,卷起竹帘,将那只面具铺到外面的箦子上。坐下来任晚风吹着,不禁想起来很多事情。搬到西之对来后,哥哥原来的家具都维持原样,唯一带过来的只有一只中国式的双层柜。很多家具在自己成年时都换了新的,大概是觉得再这样放下去很不吉利。母亲生前所能留下的家具,也就是这么一只柜子。里面放着小时候玩的双六,丝线编织的装饰性的鞠,五月五用过的长命缕,一盒贝合,以前的日记,还有一些已经没有味道的香球。
将柜门打开来,有大卷纸放在最上面一层的小筥上,纸也有些潮,有的地方也黄了,还有很多完全没有用过。那卷纸的最上面几层,用饭粒糊着一根两端黑色中间黄色的羽毛。羽毛的一旁,贴着一朵干的樱花,樱花上本来书写着非常精妙的蝇头小字,可那花瓣枯黄后,字迹也就看不清楚了。
到这个年纪,对以前的哥哥的回忆,大部分想不起来。有些则不愿意去想,就算想起来了,也没什么感触。唯独关于这根羽毛的记忆,像蔷薇那样,总是鲜明地开在心里。沿着这唯一的线索,许多许多的以前的事,也会被带到眼前。
哥哥在最漂亮的时候,是大家的哥哥。
他说着,“早上好啊。”纵使脸上没有带笑,可能气色也不好。偏偏周遭的空气都像是会笑似的,被问候了的命妇、使女乃至洗厕人,都会报以尽可能漂亮的笑容。那么这时候非常腼腆的哥哥,也禁不住会跟着笑。
每天家里固定吃的两顿饭,有时是三顿。准备菜肴的时候,哥哥都会去厨房里提前看一下,在自己看来,倒并非是关心下人。只是他的性格非常小心,整天有一些焦虑的感觉,所以关乎“食”这件大事,一定要亲自确认才会安心。
就那样子去巡视,再回来,未免有些不近人情。哥哥因为不好意思,会对佣人们说“好了吗?”或是“完成的就一起端出来”的话。于是久而久之,哥哥的名讳都成了“体贴”的别称。
第69页
同类推荐:
【快穿】欢迎来到欲望世界、
爱欲如潮(1v1H)、
她的腰(死对头高h)、
窑子开张了、
草莓印、
辣妻束手就擒、
情色人间(脑洞向,粗口肉短篇)、
人类消失之后(nph人外)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