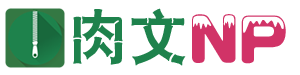内室诊断的产婆出来了,擦着手,摇了摇头。
耿夫人咬着槽牙咒骂:“丧门星,害了孩子也害了三郎,这回总算消停了。”说罢转头喊了声“来人”。
婆子进来听令,她抬手朝外指了指,“叫个牙郎来,把这贱人给我领走!”
这回是不容置疑的口吻,转头望向再要求情的儿子,在他说话之前先发了声:“你若是还舍不得她,那就和她一起走。横竖我还有你哥哥们,少了你一个,譬如没生你,你只管去吧!”
这下子没人敢说半个不字了,连耿老太太也没了声息。到底今日种种,全是因她溺爱孙子而起的,要不是她把香凝放到三郎的院子里,就没有后来这些腌臜事,郡主不会退婚,三郎也不会被砸断了臂膀。
如今可好,说不准将来是个半残,果真婚事没了,前程也没了,耿太夫人除了后悔,再也没有什么可说了。
里间响起徐香凝气息奄奄的哭声:“夫人……夫人我再也不敢了。三郎,三郎你替我求求情……”
两个婆子把人从床上拽了下来,她还在流着血,可谁也不在乎她的死活,只听耿夫人说:“仔细些,别弄脏了屋子。”
牙郎很快就来了,人成了这样,一般都是白送。毕竟做这种生意存在风险,说不定钱没赚着人就死了,还要赔上几天给她吃喝的开销,因此一般牙郎并不愿意接手这类买卖。
也就是老主顾,带一带吧,牙郎看着这半死不活的女人摇头,“卖给人家当粗使,只怕人也未必要,看看能不能卖到外埠去吧。”
如今她在耿家人眼里成了破烂,耿节使直挥手,“不拘你卖到哪里去,赶紧把人弄走。”
边上的婆子女使们看着,不免生出些恻隐之心,虽说一切都是她咎由自取,但人刚小产就被拖出去发卖,又在这数九严寒的时节下,恐怕想活命是不能够了。
那个和她海誓山盟的男人,终究没能依靠上,眼睁睁看着她被牙郎拉走了。
人走后,地上滚落了她插在发髻上的翠玉一丈青1,耿夫人见了,一脚便将这东西踩断了,吩咐家下众人:“往后谁也不许提那贱人的名字,要是让我知道了,就和她一样下场!”
众人自然诺诺答应。
耿节使和耿夫人回到上房,各自坐在圈椅里生气。
耿夫人满腹的牢骚,恨道:“不知上世里造了什么孽,这辈子遇见这样的事。这会儿可痛快了,弄得上京无人不知无人不晓,孩子没了,胳膊也成了那样……”说着抽出帕子痛哭不已,“我这满肚子的委屈,可同谁去说,好好的孩子,就这么毁了!”
耿节使一声接着一声地叹气,“行了,命该如此,怨不得别人。”
“怨不得别人?”耿夫人拔高了嗓门道,“不该怪咱们老太太?你是个大孝子,看着你母亲把三哥儿祸害成这样,也不吱一声,唯恐损了你们母子之情。我却要说,我们三哥儿全毁在她手里了。还有那李家!竟是怎么商讨都没用,今日登门见了他家贵太夫人,只差给人跪下,好话没听着半句,反给奚落得抬不起头来,我这辈子没受过这么大的屈辱。”
耿节使冷着脸,阴霾渐次布满他的眉目,半晌哼了一声,“李臣简……路还长着呢,且走着瞧吧!”
第82章 我等着天晴地朗的那一日……
***
发生了那么大的事,耿家都成了笑谈,李臣简回来的路上,正巧碰见通房跳角楼的闹剧,便让辟邪将车停在一旁,远远看了一阵。
“公爷是瞧着她跳下来的?”云畔有些怅然,喃喃说,“出身不好的女子,也有可怜之处,一个名分要靠命去挣,结果弄得这样。”
太夫人说错了,“要名分本不为过,过就过在心气儿太高。她肚子里怀着孩子,难道耿家会让庶子的生母不明不白吗,好赖会给她个正经出处的。可她这么闹,怕不是只想当妾室,而是打着当正室夫人的主意吧!”
惠存听了,暗暗朝云畔吐了吐舌头,“是不是我鼓动得她太过,把人给害了?”
云畔摇了摇头,也不能说鼓动得太过,是这徐香凝自己没有权衡,就如太夫人说的,心气儿太高的缘故。
王妃说:“咱们进香回来,就听说那通房给发卖了。才掉了孩子,也不容人把身子养好,这不是存心要她的命吗,这耿夫人也是个狠人,下得去那手。”
惠存心里终究存着三分愧疚,犹豫道:“要不咱们打听打听,她如今人在哪里,花钱把她买下来吧,也算救了人家一命。”
云畔抬起头,看了看太夫人,又看了看王妃,不知那二位是什么想法。
结果自然遭王妃反对,“你一个闺阁女孩儿,管那闲事做什么?她怀了你未婚夫的孩子,又挣名分大动干戈闹得名满上京,你该庆幸自己没有嫁进耿家,否则遇见这样的妾室,你这一辈子都得鸡飞狗跳。你如今还去救人家?我瞧你是把脑子冻傻了!”
惠存挨了数落,不敢反驳,巴巴儿看看祖母。
太夫人夹了一块白燠肉放进她碗碟里,打着马虎眼,“快吃快吃,蘸韭花酱,味道最正。”
惠存没办法,自是不敢再多言了,反正王妃的意思是休管他人瓦上霜,再说这徐香凝本就不是什么好货色,倘或心不贪,也不至于落得这样下场。
后来一顿饭罢,一家人又对坐着吃了香饮子,哥哥和嫂子行礼告退,回他们的院子去了,惠存忙站起身也辞了出来,顺着木廊追上去,叫住了云畔。
云畔回身望,见她匆匆赶过来,便问:“怎么了?有事要托付我?”
惠存支吾了下,又觑了觑兄长。
李臣简知道她们有话要说,背着手慢慢向前踱去,只听惠存叫了声阿嫂,“那个徐香凝……”然后便是唧唧哝哝的咬耳朵,再也听不真切了。
云畔认真听她说完,笑道:“我知道你的好心,我也觉得她可怜,纵是你不说,我也打算帮她一把。只是这样品性的人,沾染是沾染不得的,谁也不知道她存的什么心。我想着,打发人把她赎出来,另赁一处屋子让她养身子。等她恢复了元气,到时候就让她奔自己的前程去吧,咱们帮人帮到这里,也就差不多了。”
惠存一听,高兴不已,拉着她的手说:“多谢阿嫂,你是世上最善心的阿嫂。”
云畔抿唇笑了笑,自她当上公爵夫人,诸事都求小心谨慎,其实慢慢已经失了本心,变得水火不侵起来。自己虽是不愿意的,却也没有办法,谁让现在处境维艰。唯有在这种小地方花些钱,无伤大雅地救下一条人命,似乎并不损害她的口碑。因此在惠存抱着她一通撒娇的时候,她便憨憨地笑着,自觉十分受用。
姑嫂两个又商议一阵,才各自回各自的院子。
李臣简听见她脚步匆匆赶上来,回头问:“她又缠着你救那通房?”
云畔嗯了声,“惠存觉得她实在可怜,刚没了孩子,又给发卖了,怕她活不下去。”
李臣简脸上显出一种无奈的神情来,“真不明白你们这些女孩子整日在想些什么,一会儿捉奸,恨不得将人凌迟,一会儿又同情人家,要救人于水火。”
云畔笑着说:“公爷不懂,女孩儿也有女孩儿的道义江湖。有分寸地帮人一把,对咱们来说是举手之劳,对旁人可能是活命的机会。”
李臣简听了,才发现女孩子的世界原来也有热血。以前他并不懂得女人,以为大多姑娘只沉溺于春花秋月里,本能地趋吉避凶,现在看来好像不全是。譬如他的妻子,是他阅不尽的一幅长卷,如千里江山一样,一重有一重的风景。她的审时度势、她的蕙质兰心、她的善解人意、她的果决无畏,每一样都让他喜出望外。
只是遗憾……她对他总是缺乏浓烈的感情,仿佛仅仅是找到一个合适的人,相敬如宾地在一起生活。这个人可以是他,换成另一个人,问题也不大。他有时候不言不语,却耿耿于怀,好像有些庸人自扰,但不时就有这种感觉涌上心头——别人是在婚前牵肠挂肚,他却是在婚后患得患失。
想是因为太喜欢,他从来不讳言自己喜欢她,并不是一眼深爱,是那种久处不厌的难得。夫妇之间,能做到这样便够了,当然若能更深邃一些,那就更可喜了。
“明日我休沐,邀夫人出去逛逛吧!或者去拜访一下岳父大人,再去舒国公府看看姨丈和姨母。”
云畔讶异地抬起头来,他寻常总是太忙,从成婚到现在,也只新婚宴客那会儿一齐去过瓦市。平常总是他主外,自己主内,丝毫不乱。今日听他说愿意陪她出去,竟像一种额外奖励似的,她眉眼弯弯望着他问:“真的吗?说话可要算话!”
他说自然,“明日我把公务都推了,陪你一整日。”
她高兴起来,挽住了他的胳膊说:“那我想去桂园给阿娘上柱香,姨母那里我前几日去过了,倒是爹爹和金姨母,有阵子没见了,咱们去瞧瞧他们吧。”
他说好,看她笑靥如花,心里便生欢喜。
回到内室之后,她立刻让女使们预备明日要穿戴的衣裳首饰,自己一样样查看,替他选了一件鹰背褐的圆领襕袍,自己则是银褐褙子配上石英的旋裙,两套衣裳放在一起让他看,追着问他好不好。
她很懂得美,哪里有什么可挑剔!他捧场地往身上比了比,说:“甚好。”
她像个长久不出门的孩子一样,夜里竟还辗转反侧,他转过头问:“怎么了?睡不着么?”
她在昏暗中腼腆地笑了笑,“我想起要与你一起出门,不知怎么,有些睡不着。”
他一本正经“嗯”了声,“看来是不够累。”一面靠过去,紧紧挨着她,“要不要我助你累一些,好早早睡着?”
云畔一听就知道他在打什么主意,可是两个人夜夜睡在一张床上,太过纵性了,怕他身子受不住。忙闭上眼睛说不必,“我已经困了,这就睡了。”
他贴在她耳边,轻轻一笑,“夫人近来,是愈发替我着想了。”
那暧昧的语调叫人心头发慌,云畔缩了缩脖子说没有,“我是真的困了。”
“真的?”他在她耳垂上轻啮一下,“那让我搂着你睡,好不好?”
谁能拒绝魏国公的热情邀约呢,她原本是想推脱的,结果最后还是说了好。
天寒,床上已经准备了两床被子,一人一条睡得舒坦些,但听见她松了口,他很快便钻进她的被窝,心满意足把她拥在怀里,由衷感慨着:“身边有人可真好,夫人又香又软……”
自从在军中受了箭伤,他到冬日就很怕冷,当初那支箭射伤了他的肺,能活下来,也算捡着了一条命。可惜年少时寒冬腊月敢下河的豪迈,如今是再也不复得见了,这身子骨和早前相比,确实不可同日而语。
所幸有她在,她的光芒照耀了他。就这样偶尔抱一抱,他的怀里还是温暖的,可以相拥而眠。从前的自己很孤单,场面上与谁都处得好,但与谁都不真正亲厚,自从有了她,这种孤独慢慢缩减,变成一个林檎,一颗橄榄……
他们是夫妻,也是朋友。也许她有很多至交,可自己的密友,好像只有她一个。
云畔捋着他的脊背,仿佛自己细细的臂膀能给他带来温暖。后来什么时候睡着的都不知道了,反正一夜好眠,第二日起来精神很好。
待洗漱妥当,挪到外间去,一面吃酪,一面传姚嬷嬷进来说话:“郡主好心,见不得人受罪,嬷嬷今日派人跑一趟吧,找见那个牙郎,想法子把徐香凝买下来。她现在身子弱,找个地方安置她,要是能够,请人照顾她一些时日,等她缓过来,就由她去吧。”
姚嬷嬷听罢,道了声阿弥陀佛,“二位真真是菩萨心肠,要是换了旁人,管她死活才怪!”
“总是一条人命。”云畔道,复想了想又吩咐,“再留些现银子给她,要吃什么要喝什么,也好差遣别人。”
姚嬷嬷应了声是,“不过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,又掉了孩子,虽保住了命,将来也是一身的病,医也医不好了。终是夫人和郡主积德行善,那我这就去办,怕万一去晚了,被人抢了先。”
云畔颔首,看着姚嬷嬷走出上房,自己坐在圈椅里也思量,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,徐香凝先前做通房是身不由己,但后来怀孕、跳角楼都是自己选的,一步错,步步错,最后竟弄成了这个样子,实在令人唏嘘。
李臣简换好了衣裳从里头出来,见她坐在圈椅里出神,过去碰了下她的肩,“怎么了?”
云畔回过神来,哦了声道:“没什么,我才打发嬷嬷出去办事来着。公爷先吃点东西,我已经让人过侯府传话了,金姨母知道了,必定会先筹备起来的。”
时至今日,就算金胜玉已经过门成了侯府的当家主母,自己在称呼上仍旧改不过来,还是管她叫姨母。在自己心里,母亲终归只有一个,再也没法那样叫别人了。因这事她同金胜玉告过罪,金胜玉也能理解,到底她生母是县主,就是照着出身来看,也没人当得起她一声母亲。
因李臣简今日不必上朝,早晨的时光可以不紧不慢地安排。
两个人吃过了早点,让人将带去侯府的礼物都装了车,先往桂园去了一趟,给阿娘进了香。待磕过头,云畔也和阿娘说几句体己话,说爹爹如今很安分,后来的续弦夫人掌家是把好手,家业把持得滴水不漏,早前半败的侯府,如今已经有了新气象。
夫妇两个蹲在火盆前烧纸,火光掬了满怀。
李臣简一直等她说一说自己的境况,可她似乎把自己忘了。
“岳母大人应当更关心你是否安好。”他委婉地提点了一下。
“我么?”云畔笑了笑,“我人到了这里,阿娘见了,就知道我很好。我每常想,果真阿娘把未享尽的福都给了我,我总怀愧疚之心,觉得我现在这样的日子,是拿阿娘的寿元换的。”
他惊讶于她的想法,“你其实大可不必这样想,人来世上走一遭,谁都不是谁的附庸,今世受了苦,来生上天必会补偿,和儿女没什么相干。你就是你,如果你觉得现在过得很好,那是因为你自己也足够好。”
他说得一本正经,仿佛害怕她妄自菲薄。云畔笑起来,点头不迭,“我知道了,因为我原本就是好人,所以配得上现在的好日子。”说着望向阿娘的神位,真切地说,“阿娘,我真的过得很好,真的。”
这话不单她母亲听见了,他也听见了。似乎千言万语,都不及她由衷地说一句,婚后很好。
可她也有抱怨,轻声说:“就是我们公爷,实在太忙太累,我希望他常有今日这样的闲暇时候,让那些阴谋算计离他远些,让他好好松泛松泛。”
这是一个妻子最朴实的愿望,他穿过火光深深望她一眼,她低垂着眼睫,脸上有一层莫名的哀伤。
因为政局动荡,让她日日悬心了。离开桂园登车,彼此在车内静坐着,他牵过她的手握在掌心,双眼虽目视前方,但说的话却让她心头生暖。他说:“巳巳,我不知道这场风波什么时候能尘埃落定,但我答应你,等一切平稳下来,我一定守着你,好好过日子。”
如今的年月里,一个男人能答应守着你,便是最好的承诺了。云畔说好,“我等着天晴地朗的那一日。”
虽然不知道还要等多久,但好歹有个盼头么,两个人脉脉一笑,便觉得好日子就在前头了。
桂园距离侯府有一段路程,马车慢慢过去,要走上两刻钟时间。今日天气不好,阴沉沉地,好像又要下雪了,瓦市边,小食摊子上正蒸着糖糕,白色的烟雾包裹着穿行的行人,虽是赶集的时辰,好像也不如往日热闹。
顺着汴河的河堤一直往前,那是上京权贵云集的风水宝地,楚国公府就坐落在前面。他下意识朝外望了眼,正见一个人进入府门,仔细看,好像是耿煜身边副将。
云畔不知他在看什么,便顺着他的视线望过去,“楚国公府到了?”
他含糊应了声,并没有提及其他。
“前几日,有几位和楚国公夫人私交甚好的夫人上店里来,无意间说起一桩事,说楚国公近日纳了一房妾室,邓夫人正闹得不可开交。”云畔歪着脑袋说,“楚国公和这位如夫人的相遇挺有意思,说是初雪那日楚国公游汴河,画舫与另一艘画舫相撞,上面正坐着那位小娘子。想来那小娘子长得很美,楚国公一下便看上了,花了好大的力气才聘回来的,和一般秦楼楚馆的女子不一样,难怪邓夫人要闹呢。”
李臣简怡然笑了笑,收回了挑起窗帘的手,“三哥雅兴,果然多年不减。”
玲珑四犯 第67节
同类推荐:
偷奸御妹(高h)、
万人嫌摆烂后成了钓系美人、
肉文女主养成日志[快穿系统NPH]、
娇宠无边(高h父女)、
色情神豪系统让我养男人、
彩虹的尽头(西幻 1V1)、
温柔大美人的佛系快穿、
师傅不要啊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