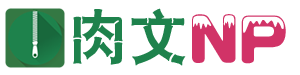“你都把了半天脉了,你……”相阙眼见相安攥着被子的手紧了紧,又听得她一会喊着凌迦的名字,一会又喊冷,遂而翻箱倒柜去找云被。
“安安无碍,不过染了风寒!过了子时,便是上弦月之日了,她的寒疾欲要发作,才会这般。”凌迦抬头望见抱着两大床云被的相阙,忍不住笑了笑,“你这两床锦被压下来,安安半条命便没了。”
“姐姐在喊冷!”相阙径直走过来,要将被子给相安盖上。
“行行行,你出去吧,安安在我身边,出不了事!”凌迦挡过相阙,觉得他简直比雪毛犼还要难缠。
“你?”相阙望着气息尚且不稳的凌迦,“你自己如今都是这幅模样,你要怎么照顾姐姐?还是我看着她吧,你且回炼丹房调息去!”
“洪莽源中,除了本君,不可能再有第二个男人能守在她床边。”说话间,凌迦已经脱了风袍。
“我是他弟弟,一母同胞的亲弟。”
凌迦也不理他,只又解开腰封,扔在床边。
“阙儿……”相安虚弱地唤了一声,顿时相阙来了精神,无比得意地冲凌迦递了个眼神。凌迦却只抬眸望了眼相安,笑了笑继续解开衣襟。
“姐姐,你哪里不舒服?”相阙小心翼翼地握过相安的手,温言道,“姐夫近日里也不太好,且让他回炼丹歇息,我陪着你可好?”
“阙儿!”相安缓缓睁开眼睛,眼峰扫过凌迦方才回到相阙身上,“你回寝殿吧,静心休息。姐姐这里有你姐夫便好。”
相阙愣了愣,半晌才“哦”了一声,慢吞吞帮把相安的手塞回锦被,掖好被角,方才不甘不愿地起身,冲凌迦翻了个白眼。
凌迦挑了挑眉,转入了内室,再出来时已经是一身寝衣,松松垮垮穿在身上,衣襟也未闭合,露出一截健硕的胸膛。
“你……”相阙惊道,“姐姐让你陪着她,你……脱衣服、你穿成这样作甚?”
“给安安治病,调理身子。”
“姐姐都这样了,你还要……你枉为神君!”
凌迦已经彻底不想再同他说话,只一拂袖将他扔出了昭煦台,瞬间闭上了两扇大门。
相安虽有些醒了,却仍旧模模糊糊,只觉心悸得厉害。不久前的梦一直徘徊在脑海中,整个人便又生出一点恐慌。此刻因凌迦半躺在床榻,伸手将她抄进臂弯,她便稍稍静下心来,往他胸膛靠了靠,待熟悉的药香弥散开来,她方才觉得心下稍安。
“可是梦魇了?”凌迦拂开她覆在鬓角的发丝,又探了探她额头,依旧一片滚烫。
“我梦见……梦见……”相安睁开双眼,只觉实在不详,复又合了眼眸道:“记不清了。只是阿诺,你可是会永远陪着我。”
“自然!”凌迦轻轻抚着她的头,“你我皆是神泽之身,千秋万载都是在一起的。”
“可是我……我找不到那一抹气泽,我好怕……”相安只觉自己明明寒气浸入骨血,内里冷的发抖,可是周身却万分灼热。而凌迦身上温冷适中,仿若一方尚好的玉石,触手生寒,却又无形中绕着一股莹润温和的气泽。
“有没有舒服些?”凌迦见她贴得自己更紧了,只微微推开她。
“嗯!你推我做什么……让我靠一靠……”相安又蹭了上来,有些委屈道。
“这是铁马冰河心法上弥散的气泽,只是为了给你退热。你别贴太近,如今我控制得不甚稳当,极易入你体内。若如此,稍后你寒疾发作时便更难受了。”
“你用心法给我退热?”相安闻言,整个人清醒了一半,翻身卷过被子,怒道:“回你的炼丹房去,不用你陪我!”
凌迦望着那一点融在被衾中的身形,连人带被捞了回来,奈何相安埋在被子里,挣扎着不愿理他,只有含糊不清的声音带着哽咽传出,“你统共就剩了那么点修为,还隔三差五以灵力给阙儿炼药……我不过是风寒,我不要……”
凌迦拨了几次被子,也没能把相安从被衾里扒开,无奈化术法掀开了一点被角,方才让她露出了头。
相安眼泪盈盈,目光迎向凌迦时,却又是一脸怒色,别过头不愿看他。
“你听我说。”凌迦从后头靠上她肩膀,伏在她耳畔哄道:“再过大半时辰,你的寒疾便发作了。我来不及给你熬退烧的汤药,你要是寒疾复发时,还发着烧,我便需聚更多的灵力化御寒之气护着你,届时我灵力损耗得更快……”
凌迦的话还没说完,相安已经掀开被子蹭回他身上,抱着她一同躺下。然后又退开了些,仰着头颤巍巍道:“这样可以吗?不是很近,我就碰到你一点点!”
凌迦手掌覆在她后背第二节 脊骨处,将她往身侧又揽回一点,笑道:“还可再近些,也无妨!”
相安躬着身子,只有面庞贴在凌迦胸膛,身体其他部位都尽可能不碰到他。她希望自己快点退烧,能恢复一点力气,然后她便可以练一夜御寒剑法,挡过半日寒疾,也免得他再耗灵力。
她寻找半年,翻遍洪莽源,都搜不到那一抹红尘浊气。而这半年里,凌迦尚且来不及复原修为,相阙却已三次被体内最后一重气泽所控,一次差点失手伤到她,一次出海伤了沿岸数百生灵。至此,凌迦开始以灵力给相阙制药,自己便开始越来越虚弱。
她缩在凌迦怀里,周身开始发汗,人亦清醒了些,终于鼓起勇气开口道:“阿诺,若阙儿再伤及无辜,就不救他了,我会动杀了他。”
“你们倒还真是亲姐弟,昨日里他同我说过这事了,要我拍碎他!”凌迦侧身拣了方帕子,给相安把额上薄汗擦去,“如此,我自然无需再费心炼药。但是随着他身死魂消,他体内那抹怨气飘散开去,无影无形,以我如今的修为根本不能及时捕获。届时这怨泽之气同游荡在洪莽原中的红尘浊气相结合,滋生魔魇,岂不更是麻烦。若那红尘之气已在有形之物上,魔魇生形,估摸到时我需生祭了元神方能灭之了。”
“所以,只有找到那抹红尘,方是上策!左右我如今不过虚弱些,总比魂飞魄散好吧!”凌迦掌心覆在相安额上,感知她烧退的差不多了,便将她搂的紧了些,只继续道,“其他一切,你都莫想!便是找寻那气泽,你也且慢慢地。今日风寒是小,你连日操劳,忧惧堵于心口,方才会晕厥。忧思过甚,伤了肺腑便不好了……”
突然间,相安浑身抖了一下。凌迦原本覆在她后背的手尚未化出御寒之气,她已经掀了被子起身,化出月剑往外走去。
“做什么?”凌迦惊了惊。
“我练剑去,可以驱寒!”
“练什么剑,三更半夜……”凌迦一把将她拉了回来。相安周身寒气本就已经开始蔓延开来,只暗里控制着颤抖。凌迦如此一拽,便彻底站不住,整个人倒下去。却也未感到床榻的生硬,反倒是觉得后脑一阵温热,原是凌迦怕她磕到,早已防备着托起她头。然而她尚未反应过来,凌迦便倾身压了上来,因他穿着寝衣,衣襟更是一直敞着,如此相安整张脸便被他按入胸膛。
“别……我练会剑便好……你别再化御寒之气了……”相安只觉周身寒气退下一些,丝丝暖流蔓延开来。
“你别去练剑,我也不化御寒之气,各退一步可好?”凌迦抽回那只抚在她后脑的手,拉过玉枕给她枕好,稀稀落落的吻滑过相安额头鬓角,至耳垂时竟启口含住了片刻方才稍稍退开了些,低头望着明明已经退烧,面色却再次酡红的相安。
“嗯……我不去……”相安也不知何时起,周身一阵酥麻,浑身抖的更厉害些,却又觉得不是因为冷,只迷糊着双眼断断续续道,“你个骗子……你说话不算话……你别化御寒之气了……抱一抱……抱一抱我便好……”
“本君一诺千金,如何便是骗子了!当真是半点气泽也没化……”言语间,凌迦手中捻了个诀,撤下帷帐,熄了灯火,换了个舒服的姿势重新抱起她。
“你……”相安皱了皱眉,忍过一点痛意,片刻间直觉体内蓦然弥散开丝丝暖意,虽不如御寒之气那般磅礴温暖,却足以扛过寒气的蔓延。
“可有暖和些?”
“嗯……”
相安话音落下,凌迦一直揽在她腰间的手稍一用力,便将她彻底搂紧了,半点间隙都没有。
一瞬间,七海之上,再次掀起浪潮,勾起九天荒火,连绵彼伏,愈见汹涌。
昭煦台中,相安一声闷哼,生生咽下了本该破口的叫唤声。满目含春的眸子里想要攒出一点怒色,瞪一瞪伏在身上的男子,却在和他四目相视的一瞬里,彻底沦陷下去。
“忍着做什么?”凌迦从头到脚没一处是安分的,口中言语落下,“不久前这般,满殿皆是夫人的声音,我觉得甚好!”
“阙儿说的没错……”相安喘息道,“你……枉为神君!”
“此刻,不许提别的男人!”
“他……是我弟弟!”
“那也是男人!”
“……”
亦不知过了多久,七海潮水退,浪涛息,海天分离开来,复了清明之态。却听殿内男子声音响起,“夫人,我当真是累了,你能否夸一夸我?”
“夸你什么?乘人之危?我若持君威,此等行径,便该将你罚至苍梧之野面壁!”
“卸磨杀驴,少主好手段……”
“那个……夫君,下月我寒疾发作……你别化气泽了,我也不去练剑,我们还这样,好不好……”
彼此心悦的两人,短暂得忘却了周遭的困顿。天色稍明时,邯穆来报,说北海水君拂章有急事启奏。凌迦同相安自是以为寻找的那抹气泽有了线索,匆匆上殿方知无甚关系,但也算有所联系,亦算得一件喜事。
原是白姮同拂章结伴寻找气泽,拂章不慎,于妖族之地误闯金光塔,中了塔里的“千媚”瘴气,白姮心急救她,以身相诱,引出了瘴气,只是如今亦还受着伤躺在北海。而两人本就倾心,经此一役,便彻底交了心。拂章更是磊落君子,留了白姮于北海,亦不想她造人非议,故而决心同她成婚。如此呈了卷宗于凌迦,恳请准予。
“以身相诱——”凌迦看着卷宗,又垂眸望着殿下的拂章,只笑道,“你的心思,本君自是清楚。只是这数万年了,倒不知白姮是从何时开始的?”
拂章微红着脸,望了望正座右手处的相安,只恭敬道:“当年君后负起离殿,君上命七海齐出,我们便……”
“嗯,你本事挺大!”凌迦将卷宗扔还给拂章,“本君走失了妻子,倒便宜了你公差出海,抱得美人归……这卷宗本君不批!”
相安浑身酸痛,软绵绵靠在正座。她同白姮少年相交,向来清楚白姮的心意。本想着拂章若只因恩德娶白姮,她也是不允的。然听至最后方才明白两人亦是两情相悦,自是心中欢喜。遂而白了凌迦一眼,勉励坐直了身子,朝拂章招手道:“你且上前来!”
拂章望了眼凌迦,见他默许,遂而躬身上前。
“安安!”
“君后!”
凌迦同拂章皆惊了一惊,他们看见相安挑破了指尖血,滴于琉璃瓶内。
“将此血融于丹药中,给白姮服下。可让她早些复原!”相安将瓶子递给拂章,温言道:“则一良辰报来,我与君上亲自为尔等主婚!”
第83章 化魔5
北海之地,白姮与拂章的婚礼,因相安和凌迦的驾临,自是风光无限。只是这两位神族至尊待人一个自是万年冷肃,但能得他出海主婚,亦是天大的恩赐,故而尽管他还是一副冰冷模样,诸神不觉什么。另一个则是最温柔和善的主,神族仙界里最好说话的神女,对谁都是笑意盈盈,万仙自是如沐春风。
礼成后婚宴之上,二位待人当真极尽恩泽,可是彼此间仿若没有处说中那般和睦。莫说近身的二代正神,便是远远瞭望的小仙,亦看出一点端倪。
两人浦一踏入北海,先时是相安少主,贴着凌迦神君,一幅小心陪着不是的模样。后来因婚礼场面实在盛大,隆重奢华,宴上多灌了两口酒言语便来不及过脑的妙华山真君叹道:“北海水君这婚礼,是要奔着百年前凌迦神君的婚宴规格去的啊,真真是……真真是……”
这话原是恭维凌迦恩厚下属,然百年前毓泽晶殿的那场婚礼俨然是七海乃至整个神族仙界的禁忌,凌迦神君娶错了人,当日大婚的根本不是如今上首坐着的相安少主。
果然,本因一件衣衫而惹得自己夫君不快,哄了半天也不见好的相安,此刻闻言后,蓦然不愿再安抚。只坐正了身子,一声冷笑,“当日毓泽晶殿墨金流光,千喜盛宴,本少主可是无缘见到,更是无福消受。”
这话说的浅而淡,周边人自是听不到。而本占了上风的凌迦瞬间垂头扶额,只道:“都是我的不是,待回去我便给夫人补了这婚宴。九日流水,我让他们翻倍了贺。”
相安眼风扫过,亦未说话,只正了正衣襟,俯身想要捡起垂地的披帛,却被人一把拦住。凌迦下了座榻,自然而恭敬地替她拾了起来。
因着凌迦起身又单膝跪着,诸神自是不敢再坐,只跟着一同起身,然而尚且来不及朝相安跪下。却见得凌迦单膝而跪竟是为了捡一方披帛,捡起后放在膝上拂去了尘埃,然后重新披在了相安身上,最后从容做回了自己的位置。而那个传说中二十二万年前便爱慕神君的少主,却是看都未看他一眼,只将披帛往臂间挪了挪继续端坐于正座之上,眉宇间竟是一片桀骜与淡然。
然而,后来,诸神因着好奇,时不时朝上首望去。终于有人看见,那相安少主缓缓垂眸,嘴角逐渐噙上温柔笑意。亦有不少人看见她笼在广袖中的手探出一点,再一点,压上身畔的黑色滚金袖口。最后,好多人都看见,黑袍广袖中的手也伸出,与她十指交缠,越扣越紧。
如此喜宴之上,有新人喜结连理,亦有主上伉俪情深,自是烈火烹油的繁景与福泽。只是,在这样的盛光,有两人并不是完全的喜悦。
酒热微酣,相阙起身从侧门出了殿外。至殿门口时,还是忍不住回头望了一眼正座之上的两人。
他的姐姐,今日穿了一身雪色长裙,袖边襟口是鎏金绸纹图案,其实同她夫君的滚金流云墨色长袍相互辉映,很是般配。
他记得今日来赴宴前,那两人拌了几句嘴。原是相安觉得今日是白姮大婚,便不愿再穿如火的红衫,怕抢了新娘风头。凌迦却连这个也醋了起来,说什么“本君让你不穿红衣,你理也不理。一个属臣就让你如此费心,还要为她换身衣裳”。后来眼见相安复了往日的青衫碧纱,他便更怒了,又道:“如此衣衫,我当你会选择良辰为我而穿……”
至此,相安叹了口气,“夫君可有为我准备衣衫?你觉得我穿什么好我便穿什么?”然后那黑袍的神君便化了一套如雪的纱衣给自己的妻子,口中喃喃“你反正爱同本君唱反调,便都随了你……”
然而当相安一身白衣蹁跹出现在面前时,凌迦盯了好久,最后却装着无甚在意的样子只挑眉道:“走吧!”
他见到他们私下里同寻常夫妻一般琐碎平凡的模样,亦见得他们在诸神万仙前宝相庄严的模样,却都是相爱的模样。可是……他的目光移到凌迦身上,此刻他已经有明显的倦意,一手自是还握着相安,一手却支额,双眼微合着,面上容色不甚好看,泛出一点病态的青白。
而他自己,自踏入北海开始,便觉体内真气激荡,那一股怨泽之气仿若受到召唤,欲从体内挣脱出来。一来因着白姮喜宴,他不愿毁之,二来他见凌迦身体稍稍好些,想让他歇一歇。故而便一直忍着!
此刻,他已在殿外一处贝罗凝化的矮桌旁坐下,勉励调伏着体内气泽。
“殿下!”
一个熟悉而遥远的声音想起,相阙抬头望去,竟是一身嫁衣的白姮。她手中脱着一枚丹药,面上还是早些年前温顺的笑意,只是到底经了风霜浸染,岁月打磨,眉宇间多一股坚韧,只是隐隐杂着一分忧色。
“这是臣下自己练的药,虽不如君上的管用,却可以助你一时调息。只是臣下学艺不精,练了许久,方得一枚。”白姮转身望向凌迦处,“不然定可以为君上解忧。”
“多谢!”相阙接过丹药,随着她目光再度望去,片刻才道,“姐夫他……内里到底如何了?”
“君上一身修为大抵快要散光了!”白姮师从凌迦多年,修为之外更兼医理,自是比他人看的更清楚。她噙着泪,望着尚且平静的海底和依旧焕发生机的珊瑚贝珠,哽咽道“君上应是以丹药续着灵力,以灵力续着七海气脉。”
“他又瞒着姐姐!”
神君与我竹马又青梅 第62节
同类推荐:
饲养邪神、
合欢宗禁止内销、
浪味仙、
在旧神游戏中扮演NPC[无限]、
幼崽饲养员、
仙城之王、
失魂箫、
在废土囤货吃香喝辣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