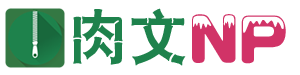刀尖顺着她的后项,在她转头之际,连绵处一条长长的血线,到侧项时,血线还是避开要害,蜿蜒着朝下而行。
本就单薄的衣襟被挑破,莹白的半边肩头在夜雨中显得尤为惑人。
一丝危险炽热的光从他眼底闪过,接着又是一串止不住的咳嗽,刀尖晃动着略提了提,他压下心绪,转了转刀柄就来回地在她身上比试着,眯着眼仿佛是在想象着将她皮肉切开的样子。
赵冉冉全然被他这副模样吓傻了,缩在地上散去了先前全部的勇气,雨势已经大到遮蔽了视线,她却连动手擦一下面上水痕都不敢,唇畔颤动着,想要发问,只是冥冥中在那等濒死的恐怖里,有种要被活埋的错觉。
落雨倾颓,列队行军的脚步声踏着水泽齐整而来。
见了这一场,阎越山微不可查得皱了下眉,他方才血战而归,上前不以为意地一甩脑袋上的血雾,谨慎地低声问:“大哥,怎么了这是,我赶紧让秦大夫瞧一瞧她?”
长刀忽然应声入鞘,段征偏过头,神色鬼魅一般地盯着他看了看,牵过侍从递来的缰绳,纵马之前,他极淡地留了句:“阎越山,你也该试着换换口味,这女人,本王送你了。”
作者有话说:
第51章 恨意
他轻声说完了这一句, 举鞭挥了下就当先朝来路回去了,留下阎越山先是‘哦’了声,望了眼地上女子的伤势,指挥两个将士就要将人拖扶起来。
等回过味来自己方才听到的, 阎越山‘啊’得愕然惊叹, 铁蹄远去, 眼前哪里还有段征的身影,他随即回头, 目光不善地去看那女人。
夜雨滂沱,但见她穿的浅色夏衫上血色晕开又被雨水冲刷,夏衫脏污凌乱得贴伏在身上,显得狼狈孱弱。
就是这么个面貌有损的女子,却惹得那么个煞神栽了两回。
阎越山赶忙移开眼, 他跟着段征这些年, 战事上屡建奇功也非是等闲人物, 不过年过三十也没个什么爱好,单就是好些女色。那些莺莺燕燕的, 他看着喜欢, 拿来消遣正合适。
万花丛中过, 说起来, 像眼前这样满腹经纶的清雅女子, 他倒是还真没玩过。
阎越山心思百转, 只是万万不敢真的照段征的话去办。
他不耐地哼了声, 随手从战马侧袋里取了块冬天的毡布,阔步上前挥退左右军士, 将那块毡布往赵冉冉半破了的夏衫上一披, 大手狠狠地又朝她胸前系了个结。
而后, 他没好气地垂眸看她:“您请吧,赵姑娘。”说实话,倘若让他先一步寻着此女,那他或许真的会不动声色地一刀结果了她。
事已至此,赵冉冉抹了把脸,乌黑的鸦睫下,一对眸子无奈惶惑,却是拢了拢那块破毡布,感激地朝身前五大三粗的男人点点头,而后认命地朝前走去。
阎越山咂咂嘴,轻咳了声转过头故作不见,这个女人,虽说容貌不怎么样,如今在他眼里却已然等同是祸国妖姬般的存在,也不知大哥究竟是怎么想的,富贵权势都得了,什么样的女人没有,偏总要同这么个女子纠缠。
雨幕中,海浪阵阵拍打岸边的礁石,回去的路上,阎越山瞧着前头艰难行路的赵冉冉,他忽然觉着,这一回或许大哥会栽得更狠。
风雨里,女子背影孱弱踉跄,可他心里却觉着,那个从来未曾动过情的,向来持刀冷厉的少年,或许才是真正的可怜人。
.
去的时候,一行人除了百余先头部队外,另还有两船五百余人的援兵。原以为总要折损过半的,可回了蕉城一清点人数,死伤约莫只有三四十个。
虽说他们早就对应海岛山地的形势,操练过数种极为合宜的武器,狼筅、□□、□□、滕盾配合有序,然而这一回横舟的意外交锋,是连段征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战果。
回到蕉城后,又接到了闽地使节递来的求和文书,这样一路大捷至此,军士们自是丝毫没有畏战疲惫的情绪,甚至军中的士气到了从未有过的盛况。
段征难得的也觉出了志得意满的快意,他一高兴,下令重赏研制武器的匠人,同时许诺三军,待战事结束,定然上奏天子,依照军功对每一个将士赐钱论功。
“那议和之事?”手下几个心腹立在蕉城府衙的花厅里,正纷纷传看闽地来的文书,“河东王此番愿割地求和,甚至还说要送质子去京城呢!”
对于闽地开出的丰厚条件,几个人围绕北地旱灾、闵粤地势、甚至还大谈起了顺天的党争来,他们跟着段征大多也才三年功夫,虽然对他阴晴不定的性子颇为忌惮,却也知道,他们这位主将是个真正惜才的。简单来说,段征身上没有他们从前上峰那样的官僚习气,行事作风虽说酷烈了些,可只要他们有功业,这位主上,待他们算得上是忠义了。
因了这个,花厅里的这些人敢当着主帅的面,就那么毫无顾虑地说着自己心中所想,议论声不多会儿就成了争辩,而段征从始至终垂眸听着,看了眼天色已晚,他起身做了个禁言的动作。
“接下和议文书,让将士们就此好生歇几日。”他已然决定了的事,也就不需的再同旁人议论,心里记挂着另一头,他一面说一面就朝花厅外头去,到门槛前时,又回头对着那些主战派说道:“快马修书上京,若能讨得八千担粮,咱们十日后开拔,去灭了白松的老巢。”
背后应和声不断,出的花厅,他对着远处看守的暗卫一挥手,一道道黑影便似鹞子般翻下屋檐消匿无踪,事涉军机,他向来是粗中有细,从不遗留任何一种可能。
另一头,早已知道他这一个决定的阎越山,正占了蕉城县令的一处私宅,酒色温柔从昨夜起他就一头沉溺进去了。
玩闹了一整个白日,他醉醺醺得才起身擦了脸,正搂着两个美艳少女叫人摆饭时,院子外头响起仆人谄媚高声的迎合声,腿上一个绿衣少女迎面朝他又喂了口酒,他不及推开,段征就从外头进来,面无表情地看着他。
“人呢?”薄唇轻启,他一身月色常服,惹的两个少女只以为是阎大将军的哪个富贵亲戚家的公子哥,不住得频频偷觑。
阎越山心里说了句果然如此,压下酒气一手一个将少女赶了下去,起身同样面无表情却恭敬道:“昨儿叫人治了伤,大哥说了那是个玩意儿,我粗人一个倒没甚兴趣,所以就给了底下人,这会儿只怕是在哪处军营里吧。”
说话间,他抬眼细望了眼前头人,但见段征神色微变,到底没说什么,只是点了点头转身就要朝外头行去。
在他抬步跨过厅堂门槛时,阎越山深吸一口气,终是没忍住,朝着他背影高声说了句:“大哥!成大业者最忌讳有命门,你我兄弟这么多年,你今日点个头,就是个手起刀落的事儿,你不忍心,我帮你去做!”
段征脚下一顿,头也不回地只说了两个字:“不必。”
见他背影转过回廊,阎越山愤然骂了两句脏话,而后他一屁股坐下,仰着脖子咕嘟嘟饮完了酒壶。
“将军哪能这样饮酒呀。”绿衣少女扭着腰咯咯笑着,上前去他舀过碗甜汤,“咦,方才那人是谁呀,恁俊俏的呦,您怎么还唤他大哥呢?”
仗着两人有过几次鱼水之欢,绿衣少女说话也并不忌讳。
然而下一瞬,她发出声短促痛呼,甜汤‘嘭’得连碗砸到了她头上,还没来得及回神时,脸上劲风袭来,她就被阎越山一个大巴掌扇到了地上。
少女被打懵了,捂着脸颊抬起泪眼去看那昨夜还同她如胶似漆的男人,控诉的目光同他微一相错后,男人眼里是毫不掩饰的冰冷杀意,她回过神连忙收起泪,当即伏在地上连连叩头哀求起来。
.
当段征快步到城南的军营时,天色已然半暗,因了他休整的军令,军营里头除了轮防值守的外,其余军士或是斗牌吃酒,或是围坐炙肉,还有的,自然是同城内几处花楼的女子寻欢呢。
他治军时严时松,只讲求实利,每每州县上有监军的文官来访时,就总觉着这处军队里透着股子匪气。
甚至因为这个,他还被参奏了几本,不过皇帝信任,也是丝毫无碍的。
入了军营,他看准了方向,脚下生风地就朝花楼女子所在之处行去。一路上,频频有参拜他的军士,他皆是挥手不语,脚下行路愈发快起来。
掀开花楼姑娘们的几处营帐时,那些日常好与女子玩乐的将士皆是一惊,他们颇为愕然地看着自家主帅,心里都在嘀咕着,这位向来洁身自好,今儿是怎么了,难不成转性了?
一连扑了几处空后,段征心下凝重,却又起了些微妙的猜测来。
他被她用药害成这样,曾想过但凡再见时,定要一寸寸亲手让她受尽痛苦而死,可是昨夜,他都试着下手了,却只是见了些血就怎么也进行不下去了。
似他这样,历经苦厄走过尸山血海,何曾有过这般难以自主的时候。
既然下不下死手,那便将她送去营中受辱。就当是回到原点,那一日,若是他们不曾相见过,或许他自己受些重伤依然能逃的命去,而她,应当早就该烂在营里了。
千人枕万人踏,这原就是她该受着的。
那般孱弱无能,那般烂好心,又怯懦面陋的一个孤身女子,在这样的乱世里,那才是她本来的命运。
他心下一遍遍同自己开解着,寻人的步子却是愈发凌乱暴躁起来,到的最后一处花楼的营帐外头,他已然怒形于色,甚至连相熟的两个将官见了,都未敢上前招呼,连忙避的远远的。
人还是没有寻着。
段征一言不发地自出了营帐,漫无目的地朝着西天边行去,天边乌云又起,这两日时近六月,南边的梅雨今年也来的早,他的心境也难以遏制得比天气更遭。
就她那副模样,若是当真叫男人欺负时,也不知会哭闹成何等样子。
眼前闪过一幕幕,有她闲坐树下看自己摘菜,有她眉目和煦笑意温柔得教他识字,更有她那一夜,泪眼朦胧得缠抱他颈项的瑟缩绚烂……
咳咳……
悔意还未升起几分,一阵撕心裂肺的咳嗽又涌了上来。一想到她为了出逃,竟会给自己吃那等阴损的剧毒,段征心头升寒,一种铺天盖地般的孤寂荒凉将他整个人包围起来。
“王爷,您可是在寻赵姑娘?”正失落荒寂间,骆彪从后头追了过来,他似是跑的颇急,邀功般地就说:“阎越山那厮叫我处置了赵姑娘,就知道您舍不得,卑职将她安置在县衙后头,同我夫人在一处呢,身上的伤也都不碍的,王爷您可放心好了……”
“是吗?”带了怒意的冷然嗤笑骤然打断了他的话,段征回过头望他一眼,歪着头两只眼就那么错也不错地乜着他。
直到他将骆彪看得心头发毛,才自顾自收了视线,又恢复了淡漠平和,也不多说什么,只压着咳吩咐了句:“送她去死牢吧,你这么聪明,该知道关她去何处吧?”
“啊?”躲过了方才那遭,骆彪苦笑着,又在心里将阎越山狠狠骂了句,仔细思索了下,还是应了句:“卑职全明白,王爷但保重身子。”
“你…”听他语意里透着堪破一切本该如此的轻巧,段征忽然觉着脸上有些挂不住,“明白些什么,说与本王听听?”
局中人糊涂,不就是千古英雄难过美人关那点子破事么。骆彪心里腹诽着,嘴上却打着哈哈一句不敢提,匆匆应了句:“卑职正要去请秦大夫,王爷的吩咐,顺道我会照办的!”
一边说着,他一边脚下生风般的一溜烟就跑远了。
.
知道了她的去处,段征悠然回了府衙用饭吃药,夜里乌云褪了些,看着天色不错,他又骑马去了城外军营同将士们一处看了两处热闹喧天的大戏。
席上相熟的几个旧日兄弟都不在,他孤零零一个坐在台前最好的位置上,将士们虽敬重爱戴他,可这样私下休整的场合里,实在并不乐意见着他。
也是觉察到气氛有异,台上吹拉弹唱几遭儿折子戏过了,正唱至梁红玉击鼓战金山,段征忽然便觉着索然无味起来,心里头孤寂愈发纠缠着难以驱散。
他呼喇一下站起身,吓得周围将士以为出了什么事,先是离着近的两个副帅提了兵器跟着起来,而后潮水一般,一圈圈向外头漫开去,营帐外看戏宴饮的千余名将士尽数跟着起身,吓得台上唱戏的‘梁红玉’愣着眼也一并停了战鼓唱词。
没成想自己一个动作引来这么大动静,段征定下神,慨叹着朝一名副帅点点头,浅笑了下示意他无事后,便径直越过戏台,捡了条无人的小道就离了场。
那副帅只见过他杀伐冲锋时的狠劲,哪里见过他这般温和柔情的神色,一时间愣了好半晌后,简直以为自己是喝多了疯魔了,看着主帅走远了,他才狠命一拍脑袋,举刀朝天咧着嗓子喊道:“都他娘别站着啦,坐坐坐!今夜该咱们歇着,外头兄弟值守着呢,都坐下!”
.
城东的牢狱离着城南扎营处不远,纵马过去加上守城盘查的时辰也不过是二刻多些。
段征下马时,早已得骆彪授意的一名部将过来牵缰,不待他开口,那人便秉告说:“骆大人说他夫人在县里候着他回去呢,人已经带来了,就在里头,王爷您去了就见着了。”
蕉城是闽北靠海一座大城,城东牢狱始建于前朝,除了地上两层官吏的办事值守处外,所有牢房都建在地底下,竟是一共造了五层,当时延请了最好的工匠,每层皆高二丈,通风豁口也造设的隐秘完备,依着罪行刑期的轻重,囚犯分属不同的地层,越是往下,便越是守卫重重,插翅难飞。
第五层地牢专供死囚所用,因着整间地牢的覆斗状形制,这最下一层也是占地最小,分了东西四处,不过寥寥二十余间暗室。
此刻,原本的死囚都早已被征发守城战死,赵冉冉缩在东南边最靠里的一间不大的牢房里,抱臂坐在墙角的枯黄脏乱的杂草上,正不住得开导安抚自己。
方才她进来的时候,在入口处的刑架上,赫然见到了昏睡不醒的薛稷。但见他身上也无伤处,可她焦急地连唤了好几下,也不见他动弹,也不知他们究竟是喂他吃了什么。
这处的牢房四壁被遮得严严实实,除了几个通风口外,只在朝着甬道的外墙上开了一道仅够一人通行的铁门。
暗室里空气逼仄,那些人虽对她还算客气,却连一盏油灯都未曾给她。
这里四壁空空,寝具桌椅一样也无,唯一的光亮便是从铁皮门用于递饭的小窗边传进来的火光。
她方才趴在门边,试图朝外看一看薛稷的位置,徒然惶恐间,倚着阴寒石墙坐下时,便在门上瞧见了许多陈年的斑驳血迹,似乎还有指甲抓挠的痕迹。
不难想象,这都是从前那些罪行滔天的死囚们,最后的怨气与不甘,那些人□□掳掠,杀人越货,或许大多都是穷凶极恶之徒。
环顾幽暗阴森的四壁,赵冉冉只是在此呆了一个时辰,胡思乱想间,心头便涌上森寒惧意。她不知薛稷是怎么落到了这处来的,也不知他一动不动的究竟是遭遇了什么。
置身于此,她能做的只有等待了。
想明白这个后,她强压下满腔的不安忧惧,迫着自己去草垛上靠一靠歇一会儿。
才刚坐定时,手上忽然一阵作痒,她恍惚着抬腕一瞧时,但见是一只寸长的百足虫,正扭捏着硕大的身子附在她手背上。
百足虫的速度实在是快,不过眨眼的功夫,就已然从手背窜到了腕上,她从前最怕这些个,当即尖叫了声,跳起来拼命甩手。
死牢不大,这一声惧意十足的惊叫,在段征刚低头跨进门边时,完完整整得落进了他耳朵里。
越过刑架上的薛稷,他几乎想也不想地皱起眉,按刀阔步就循声到了最里头那间。
在狱卒开门的一瞬间,赵冉冉刚好将百足虫甩落到地上,吓得满目水色得惊讶回头,乍亮的火光刺得她水眸一掩,两滴清泪赶巧就顺着面额坠落下去。
--
丑妻难追 第39节
同类推荐:
偷奸御妹(高h)、
万人嫌摆烂后成了钓系美人、
肉文女主养成日志[快穿系统NPH]、
娇宠无边(高h父女)、
色情神豪系统让我养男人、
彩虹的尽头(西幻 1V1)、
温柔大美人的佛系快穿、
师傅不要啊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