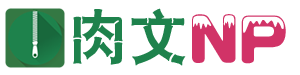*
烛台在五更天时终于尽了,内院中的沙沙声里参杂着啜泣,不知道谁开了个头,哭声愈发大了。
家仆家眷全在后头哭,吵得他更为心烦意乱。
身边围着兵士,刀锋麻木对准众人,他忍不住要回身呵斥,身形一动,刀锋便更近几分。
家眷们哪里见过这种架势,哭声抖如落叶,他只对上妻子哭红的眼,狠话从嗓子眼变成无奈的苛责——“你们就,省点力气吧!”
他一生戎马,如今却落个罪臣的名头。
罪臣,罪臣,何罪之有?!
他弓下腰,咬得下唇渗血,粗硬的指甲要将掌心掐出深深的印子。
“辛大人。”
他的影子落在一双薄底轻靴上。
辛从修游魂似地抬头,先瞧见那人腰间月牙形的雪玉,分明素白的一身,袖底却讲究,随着他动作,几瓣青莲绽放在他袖间。
只是这人模样生得清俊,眼底却是淡漠至极。
他才明白自己是死期将近。
辛从修咬牙,强迫自己要看开了来:“我什么都不会说的。”
篝火啪地爆破一声。
“我知道。”姚咸负手而立,仿佛对他的话早有预料,扫一眼后方,轻声问,“谁先来?”
后面的人本缩着啜泣,听到他的话,转而哭得撕心裂肺。
哭声如一把把刀割破耳膜,血液在身体里流的飞快,快得涌上脑门,辛从修蓦地得张眼,刷地以矫健的身手跃起,就近夺了一把刀。
其余部下飞扑而上。
姚咸轻轻抬手,止了他们动作。
只见辛从修眸中赤红一片,竟是一人一刀,先杀了自己的夫人和小妾,再将亲近的家仆杀尽……
他本就是武将,杀敌不眨眼。
“臣身为朝臣,利欲熏心,是一罪,身为辅佐,未对王侯劝诫,是一罪,臣身为楚人,未对百姓负责,致使乡民惨死,是一罪!罪臣痛之悲之,身陷牢狱,万死难辞其咎,所有罪行皆为我一人所为……“
血将院子里的草地都染红了,他徐徐跪下,不知对谁说,”罪臣,无话可说!”
“辛大人何苦。”
姚咸旁观许久,才幽幽叹了一口气,语气又轻又淡,“伏罪纸上几个字而已,何必费如此周章……可惜,这孩子怕是辛家唯一的血脉了……”
辛从修错愕抬头,只见姚咸身后牵出一个幼童。
他模样痴傻在咬手指,对父亲的举动一无所知。
辛从修呼吸顿急,不由后退几步,“他才五岁,你们,怎能拿孩童做威胁……”
姚咸不为所动,推着孩子的背,“去吧。”
孩童叁两步就到他跟前,眼珠子只顾着好奇四周,就是落不到自己父亲身上。
辛从修抖着揽他入怀,声音几不可闻,“怪爹不好,怪爹…………”他眼里泪意涌动,孩子一下就被抓痛哭,他在哭声中闭眼:”写多少,我也难逃一死,我儿一生痴傻,没了辛氏庇佑,又如何能活!“
“我可以将他从去善署,改名换姓,再寻一户寻常人家,安稳度过余生。”
“此话当真?”
“当真。”
死一般的沉寂后,“好……”辛从修艰难吐出一个字来。
雪白的纸张抖动,他抖擞落笔。
墨迹未干便被人收走,他浑身没了气力,“我想,留个全尸。”
姚咸甚至连眼都不曾眨一下,说可以。
他亲自倒了一杯酒,“请。”
最普通的酒液,却是催命的毒。
“以命报君侯,恐有罪……”辛从修目眦欲裂,夺过来一口灌下,不过半刻,只觉胃里翻滚,黑色的血液从耳孔流出。
“吾魂魄……悔矣……”血沫子喷出,人软软倒下。
风过,带走所有生机。
小孩子在血污里过来,忽然伸手抓住一方衣角。
姚咸蹲下来,不见嫌弃,温声问:“好孩子,叫什么名字?”
孩童咿咿呀呀说不出话。
“嗯,这样啊……”姚咸温柔应答,轻轻拂开他的手,只说,“下辈子,投个普通人家吧。”
他起身离开,身后银光一闪,只余园中寂静如修罗场。
……
门轻轻叩响叁下。
“进。”
玄衣广袖下执笔有力,朱笔又一道划下披红,熊良景没抬头,“如何了?”
“共叁十八家,问审正法十六家,供罪叁十四家,不知道此册中,可有世子想要的结果?”姚咸上前将一锦匣交给他。
里头躺着一本册子,薄薄几页纸,世子却看了许久,他凝视着上头的字迹,似在斟酌。
烛台上的火苗轻动,在他俊郎的脸上轻轻地摇曳,他合上册子,“甚好。”
“多谢渊君相助,我这就修书让你回渊,如何?”
良景看姚咸的表情,”怎么,渊君不愿?“
姚咸道:不够。
良景直起腰,眉间一挑,玩笑似的语气:“是要借兵助你夺位,还是要什么?”
姚咸道:“世子说笑,泽钰只是在大楚,还有些未竟之事。”
良景点首,“这未竟之事,渊君怕是不肯同我说了。”他站起来,眼睛还看着姚咸。
从姚咸进门就在端详,或者说从见面开始,他就开始揣摩,审视。
但,仍猜不透。
矫揉造作的公子哥他见太多,鲜少遇到如此的人。
纤秀,孱弱,却沉稳。
熊良景将册子收到一边,踱步从案后出来,“虽武平君势力将将扫清,也仍有追随之辈,不乏重臣,若他们抗命不遵,届时军心动荡,难免动摇楚国疆土的根基,实在头疼……”
良景以指尖扫过雪片似的奏疏,又负气似的推开,“剩下的人,却只会争权夺势,盯着一个空着多年的位置吵个不停!”他望向姚咸,“你觉得,该不该重启这个位置?”
姚咸道:“蔺相之后,相位空缺多年,薛氏已成王亲,定是相位人选,朝中鄢候为国公,本该与武平君分庭抗礼,如今平候势力扫清,薛氏将为不二人选,只是……”
“只是什么?”
“世子同夫人伉俪情深,应当庆幸,无人敢在上头写上薛氏二字,毕竟桐乡为薛氏封地,而难民一事,怕要难辞其咎……”
一阵肃杀般的静。
“渊君看得倒是真切。”良景嘴角往下一沉,“你以为,这伏罪状上,我要看见的是谁的名字?”
姚咸音调平和,不急不惧:“泽钰不知。”
世子露出一丝冷笑:“是不知,还是不敢?”
姚咸仍不言语。
“我许你无罪呢?告诉我。”
“成大功者,在因可乘之机而遂狠心,无论名册上有谁,世子心中所想为何,便出现什么。”
屋内有片刻的安静,随后一声嗤道:“好一个狠心!”
姚咸轻笑,一双眼睛在灯下如珍珠般温润:“泽钰只是看多了几步,再远些,也力不能及。”
真是滴水不漏,反而令人不安。
熊良景不愿再与他交谈,便遣了他离开。
眼见姚咸身影要消失,又冷不丁开口——“我不会将阿芙给你的。”语气斩钉截铁。
门框留下姚咸半道剪影,看不清表情也好。
想不到棒打鸳鸯的话,竟从自己口中说出,良景继续道:”我知渊君心不在此,不会甘于为质,但就算有朝一日渊君重新得势,我也不会让她远嫁的,她年纪小,尚在玩心重的,你……”
他缓了语气,“我大楚民风开放,从不以出身定论,倘若你只是寻常楚民,我自然不会过问,只是……”
他扶额,“罢了,如今她心在你这,我不想坏她心情,只要你好好待她,不要,不要让她涉入朝堂的斗争里……”
“世子不比多虑。”姚咸的声音自门后响起,”公主金枝玉叶,自然值得更好的人。”
……
夜已深,街上无人,而天上只一轮弯月,伴着稀疏的淡云,两道影子一前一后走着。
姚咸缓步走在前头,身影在夜色中显得沉郁,雪色的衣衫渗着月华,透出来几分冷凝。
玉泉跟在后头,瞧见他衣角一处淡淡的血痕,“那武平君的小头势力何其多,树大根深,今日叁家,明日不知道还余几户,公子何必都应了那世子的话,平白脏了公子的手。”
“无妨。”姚咸颔首,“倒是有些有趣的事情同你说,你可知当年,换了世子妃的事情,蔺家折辱被断了前途,其中缘由,也有平候的一份。”
“所以他这是,打算给旧情人报仇?”玉泉轻嗤,“楚世子还是个痴情种。”
“谁知道呢。”呵气有淡淡的雾,姚咸回过头来,转了话头,“说起来,我们许久不曾出来散步了。”
月色的皎洁,照着他的眼角眉梢渐渐清晰了起来,带出一抹淡笑,是温润的样子,“待平候的事情了了,许你在楚国四周散散心,如何?”
“公子。”玉泉定住步伐,那月映得地面越亮,她心中忧虑便如雾般散开,“他……能保住命么?”
他反问她:“你是想他死,还是不死?”
姚咸侧头,漫不经心地,“一个王室宗亲,若就比掉下去,落得家族惨死他独活的结局,定会让他比去死还难受。”
玉泉轻吁口气:“若能保住命,也够了,算我欠他的……”
姚咸眉头略微一拢,静默半晌才道:“好,我知道了。”
“谢公子。”
二人又陷入无言,玉泉兀自往前走,身后脚步渐渐停了,她疑惑回过头去,只见姚咸立在原处,目光一瞬不瞬望着岔口,面上罕有的,露出一丝苦恼。
玉泉皱眉问,“公子这是要去哪里?”又看着通往的地方,霎时想到了什么,乍然回过神来,“离武平君叛宫也过了十几日了,公子被这楚世子说几句,是被说中了?”
姚咸笑笑,起脚竟真的要前往。
玉泉急了:“公子!”
她扯住他,衣袖内的手在轻颤,“如今也算是搭上楚君这艘船,就该和她断了……”冷艳的脸上也渐渐泛起了惊疑,“公子莫不是忘了其中滋味,慕容的事,公子要重蹈覆辙?”
话一出口,玉泉心头也凉了一片。
慕容二字,提不得。
她紧抿了唇瓣,见姚咸慢慢收敛起面上的笑意,他问:“玉泉,我待你如何?”
玉泉竟一点都不敢再看他,生怕他接下来的话要戳她心肺。
她喉头哽结,“公子,待我很好,是公子将我从大公子手里救出来,我不会忘记……”
姚咸瞧着她,眼神平静:“是么。”
玉泉松开手,低首道:“是。”
”若觉得在我身边不开心,你大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,我不会加以阻拦,只是……”姚咸轻轻勾嘴角,眼底没有笑意,“也希望你不要干涉我的事情,好么?”
礼貌,却是最致命的疏远。
玉泉错愕无言。
一阵风过,她便再也瞧不见他身影。
48月空明(上)
同类推荐:
【快穿】欢迎来到欲望世界、
她的腰(死对头高h)、
窑子开张了、
草莓印、
辣妻束手就擒、
情色人间(脑洞向,粗口肉短篇)、
人类消失之后(nph人外)、
不小心和储备粮搞在一起了(西幻)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