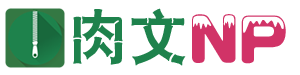就在宋巩即将踏入南园之时,一声“爹”忽然从身后传来。
宋巩听得真切,那是宋慈的声音。他急忙回头,只见迷蒙雾气之中,一道人影走来,正是宋慈。
“慈儿……”他原以为宋慈昨晚便已逃离临安,哪知这时竟会在南园外见到,一时惊在了原地。
夏震一挥手,看守大门的几个甲士立刻冲上前去,将宋慈拿下。宋慈镇定如常,声音平静:“夏虞候,韩太师想见的人是我,还请不要为难我爹。”
“你来了就好,太师已等你多时。”夏震吩咐那几个眼线,将宋巩带到许闲堂看管起来,再让甲士押着宋慈,随他前去归耕之庄见韩侂胄。
“慈儿……你怎么回来了?”宋巩被强行带入许闲堂时,诧异不解地望着宋慈。
“爹,你安心在此等候,不必担忧。”宋慈不做解释,留下这话,由甲士押行而去。
韩侂胄吩咐完夏震后,只不过一盏茶的工夫,就见夏震返回,带来的却不是宋巩,而是宋慈。他心知自己没有料错,宋慈到底不肯贪生舍义,冷淡地笑了一下,道:“你昨晚既已离开,为何又要回来?”
“宋慈特来谢过太师。”宋慈被带到离韩侂胄一丈开外,站定在那里。夏震吩咐押行宋慈的甲士退出归耕之庄,只他一人留守于韩侂胄身边。
“谢我?”韩侂胄将手炉放在一边,身子稍向后仰,靠在了椅背上。
“谢太师许我出狱一日,让我得有机会,查破亡母一案。”宋慈说这话时,向韩侂胄行了一礼。
此事早有眼线来禀报过,韩侂胄昨天便已知晓。
“你这人很有意思。”韩侂胄道,“好言相劝时,你目中无人,以为你傲骨铮铮,却又如此恭敬端正。”
宋慈一礼行毕,道:“亡母一案虽破,但仍有不少存疑之处,须向太师言明。”他目光直直地看向韩侂胄,“这起案子并不复杂,现场留下了不少痕迹,可以轻易查出真凶是窃贼吴大六,然而当年府衙遮遮掩掩,不是查不清楚,而是根本没去查,使吴大六得以逍遥法外十五年。吴大六无权无势,一个外来之人,在临安城中没有任何根基,何以府衙却要替他遮掩?只因此案凶手不止一人,在吴大六之前,还有一人曾潜入客房对我娘亲行凶,被吴大六瞧见。府衙要掩护的,其实是这前一个行凶之人。此人姓虫名达,是后来的池州御前诸军副都统制,当年则是太师的下属。”
韩侂胄脸色一沉,道:“你来见我,是为了你娘的案子?”
“慈孝之心,人皆有之,母亲枉死,不敢不查。”宋慈说道,“吴大六虽未目睹虫达的容貌,但看见其右手断去末尾二指,加之当时仵作祁驼子验得我娘亲右腹遭短刀捅刺,伤口长约一寸,而虫达正好随身携带有短刀一柄,我曾亲眼看见过,其刀宽正在一寸左右,且事后虫达威胁家父离开临安时,承认他自己便是凶手,可见前一个闯入客房对我娘亲行凶之人,正是虫达。”
他继续道:“可虫达何以要对我娘亲行凶?当年我随父母来到临安,曾与太师的公子韩结过怨,虫达若是为了替韩报复私怨,该来杀我才是,不该对我娘亲下手,而且他有的是机会动手,大可不必选择大白天里,在人流甚多的锦绣客舍里杀人。”
说到这里,宋慈语气起疑:“更让我奇怪的是,虫达怎会在我娘亲回房之前,就提前躲入行香子房?或者该这么问,虫达如何知道我娘亲住在行香子房,提前便去藏身?直到新安郡主告诉我,当年我娘亲遇害之前,曾为了我在百戏棚被韩欺辱一事,跟随后来的恭淑皇后去过太师家中,想当面讨个说法,只可惜韩不在家中。当时太师曾向我娘亲道歉,还问明我娘亲的住处,说等韩回家之后,便带上韩亲自登门道歉。所以太师你,当年知道我娘亲的确切住处。”
韩侂胄听到这里,脸色阴沉,向夏震看了一眼,示意其退下。
夏震凑近前去,小声道:“太师,属下若是离开,只怕……”
韩侂胄只冷冷地吐出两个字:“出去。”
夏震不敢违抗,当即领命,躬身退出了归耕之庄。
韩侂胄本就是武官出身,平日闲暇之时不忘舞刀弄剑,年逾五十仍是身子强健,根本不把宋慈这个文弱书生放在眼里。更何况就在他触手可及的地方,还放置着一柄剑,正是当日宋慈去韩府花厅见他时,他曾舞弄过的那柄宝剑。宋慈距他一丈之外,但凡有任何异动,他可立即拔剑斩之,是以根本不惧与宋慈单独相处。
支走夏震后,韩侂胄冷眼瞧着宋慈,道:“你既然想说,那就接着往下说。”
宋慈看了一眼韩侂胄的右手。韩侂胄说话之时,右手有意无意地轻抚剑柄。宋慈看在眼中,不为所动,道:“我娘亲登门讨要说法之时,韩不在家中,说是随其母亲去城北郊外观赏桃花。后来我父亲在琼楼见到了赏花归来的韩,其身边有多个仆从,却没有虫达。由此可见,虫达当时应该留在了太师家中。虫达能赶在我娘亲回住处之前,抢先一步赶到锦绣客舍,翻窗潜入行香子房,只怕是太师将这一住处告知了虫达。所以虫达急着杀害我娘亲,极可能是出自太师的授意。”
韩侂胄听到这里,冷笑了一下,颇有不屑之意。
宋慈摇了摇头,道:“可我娘亲如何得罪了太师,令太师骤起杀意,而且那么着急要将我娘亲杀害?我一直想不明白。直到昨日,新安郡主遇害一案告破,凶手贾福被抓获。贾福有一大罐金银珠玉,是从其养父那里得来的,其中有几枚玉扣,与先帝赐给恭淑皇后的玉扣相似,其来源极可能是皇宫大内。我去报恩坊查问贾福的养父,竟意外得知他在宫中做过内侍,曾是古公公的下属,那一大罐金银珠玉,都是古公公所赏。这位古公公名叫古晟,新安郡主曾对我提起过,说当年我娘亲去太师家中时,刚到大门外,看见两人从太师家中出来,其中一人是时任太医丞的刘扁,另一人便是这位古公公。
“刘扁曾在十年前获赐一座宅子,开设成了医馆,也就是如今的刘太丞家。据其弟子白首乌所言,这座宅子是刘扁为当今圣上治病所受的御赏。这位古公公,大约也是同一时期,从御药院的奉御,被圣上提拔为都都知,一跃成为宦官之首,至于他给贾福养父的那一大罐金银珠玉,想必也是从圣上那里得来的御赏。此二人,一个只是翰林医官局的太医丞,一个只是御药院的奉御,有何大功,能受此厚赏?刘扁获赐那么大一座宅子,想必定是治好了什么疑难杂症,然而当时圣上即位不久,正值春秋鼎盛,没听说患过什么病。治病受赏云云,不过是刘扁的托词而已。当时朝局已安,四海承平,刘扁和古公公身在宫中,唯一能立大功的机会,只有不久之前的绍熙内禅。”
宋慈看了看四周,看了看这丹楹刻桷的归耕之庄,道:“功莫大于从龙,这南园本是高宗皇帝的别馆,太师能从太皇太后那里获赐此馆,究其根源,也是当年在绍熙内禅中立下定策之功。十五年前,圣上还是嘉王,刘扁和古公公出现在太师家中,二人离开时戴着帽子,有意将帽子压低,遮住了大半边脸,似乎不想被人认出。可当时为我娘亲领路的恭淑皇后还是认出了二人,叫破了二人的名字。二人没有说话,只是匆忙行了一下礼,便匆匆离去。这一幕正好被随后出现的太师瞧见。这二人为何要与太师私下相见?若是上门看诊,大可不必遮遮掩掩,而且只需刘扁一人即可,古公公为何要一起去?”略微一顿,语气微变,“翰林医官局掌入宫诊治,对症出方,御药院掌按验秘方,修合药剂,二者合在一处,便可为圣上施药愈疾。彼时先帝即位不久,却时常患病,正需进药诊治,然而数年下来,先帝病情非但不见好转,反而越发严重,以至于无法处理朝政。传言先帝病情时好时坏,反复无常,就算勉强上殿听政,也是目光呆滞,言行乖张。都说先帝患病,是受李皇后所迫,可一个即位之前被孝宗皇帝誉为‘英武类己’的帝王,能在短短三五年间,仅仅因为皇后所迫,便变成这般模样吗?”
宋慈话音一转,道:“刘扁后来死于牵机药中毒,此药相传是宫廷御用毒药。十年之前,刘鹊的女儿刘知母,刚住进刘太丞家不久,便无意在医馆中翻找出一瓶牵机药,误食而亡。白首乌又曾提及,刘扁在宫中做太丞时,知晓了牵机药的炼制之法,私下炼制了此药。由此可见,早在十年甚至更早之前,刘扁便已拥有牵机药。刘太丞家的二大夫羌独活,钻研毒物药用之法,私下配成了牵机药,长时间以家养之犬试药,发现牵机药虽是致死剧毒,但若少量服用,并不会致命,只会致使头目不清,出现疯癫之状。刘扁与古公公合在一处,正好可以为先帝治病进药,倘若每次进药之时,都偷偷加入少量的牵机药……”
“宋慈!”韩侂胄忽然喝道,“你可知自己在说什么?”
“我当然知道,我方才所言,便是太师千方百计想要掩盖的秘密。”宋慈环顾左右道,“此间乃太师住处,别无他人,太师又何必惧之?”
韩侂胄脸色阴沉,道:“我堂堂正正,何惧之有?只不过你娘的案子,我毫无兴趣。”身子稍稍前倾,“我只问你,东西呢?”
“太师想要的东西,昨晚之前,还不在我的手上。”宋慈道,“也是要谢太师许我出狱一日,让我得以有机会,找到虫达留下的证据。”
韩侂胄神色一紧,之前他便想过宋慈昨晚离开,必有其因,原来是找虫达留下的证据去了。他掌心一翻,道:“交出来。”
宋慈看着韩侂胄摊开的手,立在原地,不为所动。为了这个证据,他苦思冥想了许久,尤其是被关押在司理狱的半个月里,他常常在牢狱之中静坐,不知多少次思考这个证据会在何处。他一度有过怀疑,弥音之所以决绝赴死,是不是因为这个证据早已随着净慈报恩寺的大火灰飞烟灭,并没有落在弥音手中?然而他想了许久,忽然想到了一事,当初净慈报恩寺起火之时,弥音先是冲入禅房去救虫达,后又冲回寮房去救巫易。弥音死心塌地追随虫达,冒死冲入火海相救,宋慈想得明白,可弥音当真会为了救巫易,甘愿去冒被大火烧死的风险吗?巫易虽是何太骥的至交好友,但弥音与之并无深交,似乎不至于冒这么大的险。宋慈转念一想,巫易所住的那间寮房,正好也是弥音的住处,倘若弥音冲回寮房不是为了救人,而是为了救出某样东西呢?当时虫达已被刘扁认出,知道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,会不会为了以防万一,将那个至关重要的证据交给尚未暴露身份的弥音保管呢?倘若真是这样,那弥音冒死冲回寮房,也就解释得通了。
宋慈不知道自己的猜想究竟对不对,即便是对的,可弥音已经死了,既没有将证据交给他,也没有交给欧阳严语,如今这个证据落在何处,根本不得而知。他昨天去见过贾老头后,将绍熙内禅、古公公、刘扁和牵机药联系在一起,推想出了韩侂胄想要遮掩的秘密是什么。至于贾老头,作为古公公曾经的下属,能从古公公那里得到那么多金银珠玉,又对绍熙内禅讳莫如深,想来要么是参与了其中,要么便是知道这秘密后威胁了古公公。宋慈原本不再对找到那个证据抱有任何希望,打算昨晚就去见韩侂胄,甚至为此交还学牒退了学,去见了同斋和真德秀最后一面,已做好了有去无回的准备。然而昨晚回到太学后,目睹孙老头和几个斋仆为了栽种松柏而挖地,他突然想到了最后一次在望仙客栈见弥音时,弥音曾对他说过的一句话:“我能告诉你的,都已经告诉你了,你真有查案之心,那这个秘密,你就自己去挖出来吧。”
他当初在望仙客栈里听到这话时,便觉得弥音这话听起来有些怪怪的,至于怪在哪里,他一时没有想明白。直到昨晚看见孙老头挖地,他忽然想起了这句话,倘若弥音所说的这个“挖”字,不是追查的意思,而就是挖掘的本意呢?会不会弥音早就告诉过他某个地点,暗示他去挖掘呢?他想了一阵,最终想起了弥音说过的一句话:“狐死首丘,入土为安,只可惜我和太骥再也不能归葬故里。”
狐死首丘,是传言狐狸将死之时,会把头朝向狐穴所在的山丘,意即思念故乡。弥音的这句话,似乎是在说自己决意赴死,只可惜他和何太骥一样,不能归葬故乡。弥音的尸体最终会葬在何处,宋慈不得而知,弥音自己更不可能知道,但何太骥葬在何地,弥音和宋慈却都是知道的。何太骥正是因为拿虫达留下的证据去威胁韩侂胄,最终丢掉了性命,那弥音会不会将这个证据与何太骥埋在了一起呢?这个念头一冒出来,宋慈当即决定,去何太骥的墓地寻个究竟。
这个证据极为重要,宋慈也担心韩侂胄派了盯梢之人,生怕自己直接去净慈报恩寺后山寻找证据,会被人跟踪发现,他可不想刚找出这个证据,便被韩侂胄得到。所以他回了一趟梅氏榻房,说他想明白了要出城,让桑榆帮他乔装打扮,并混在桑氏父女和几个货郎之中,成功避过了韩侂胄派来的眼线,离开了榻房,从钱塘门出了城。出城之后,宋慈让桑榆和桑老丈回去,但桑榆不放心,要多送他一程,竟一路送过了整个西湖,来到了净慈报恩寺脚下。宋慈请桑榆和桑老丈止步,随即提着一盏灯笼,舍弃大道,往净慈报恩寺旁边的山路走去。桑榆本以为宋慈是要离开临安,可那条山路通往净慈报恩寺后山,根本不是离开临安的道路。桑榆急忙追上,比画手势,问宋慈要去哪里。宋慈这才道出实情,说他为了查案,要连夜去一趟净慈报恩寺后山。
桑榆本来因为离别在即,心头失落,这一下又是惊讶,又是担心。她望了一眼后山,黑漆漆的,宋慈独自一人前去,万一遇到什么危险,如何是好?夜里山路不好走,她让年事已高的桑老丈留在净慈报恩寺外等待,她则跟着宋慈走上了那条山路。宋慈知道桑榆的心意,没有加以阻止。
来到后山之上,在距离原来巫易的坟墓不远之处,宋慈找到了何太骥的墓地。宋慈从怀中取出了一柄很小的铲子,那是他之前在太学回梅氏榻房的路上买来的,比他上次墓土验毒时所用的铲子还要小上一截。他围着墓地走了一圈,何太骥是一个月前下葬的,坟墓周围留有不少挖掘取土的痕迹,不可能把每一处痕迹都挖开寻找。宋慈的目光最后落在了何太骥的墓碑上,碑前插着不少燃尽的香烛头。他不知道弥音有没有来埋过证据,就算有,他也不知埋在何处,但料想弥音与何太骥的关系那么亲近,不大可能直接挖开这位侄子的坟堆,也不可能随便找个地方埋下,最有可能埋在刻有何太骥名字的墓碑之下,而且弥音来过这里,想必不会忘了祭拜这位侄子,墓碑前的那些香烛头,说不定其中就有弥音留下的。于是他俯下身子,在何太骥的墓碑前挖了起来。
桑榆站在一旁,提着灯笼照明,见宋慈一来便挖掘墓地,难免为之惊讶。这墓地位于密林之中,透着阴森,时有阵阵冷风吹过,冰寒刺骨。但桑榆并不害怕,只要宋慈平安无事地在她身边,哪怕身处黑暗阴森的墓地,她也觉得心中甚安,只是不知宋慈在挖什么,惊讶之余,又有些好奇。
宋慈挖了好一阵,挖了大约一尺见方的一个坑,铲子忽然发出了沉闷的声响,像是碰到了什么东西。他急忙将泥土刨开,一个书本大小的木盒子露了出来。他将木盒子挖出,见上面挂着一把锁,于是先用铲子敲打,后又捡来石头砸击,最终将锁砸掉了。将盒盖掀起来,里面是一团裹得方方正正的油纸,他将油纸拆开,最终看见了包裹在里面的东西——一方折叠起来的绢帛。
宋慈拿起这方绢帛,展开来,见左下角有所缺失,带有些许焦痕,似乎是被烧掉了一角。绢帛上有不少墨迹,宋慈挨近灯笼,见上面写着:“庚戌三月廿九日,会于八字桥韩宅,共扶嘉王,同保富贵,违誓背盟,不得其死。刘扁,古晟,韦……”
宋慈依着字迹看下来,绢帛上所写的是共扶嘉王赵扩的盟誓,其中庚戌年是十五年前的绍熙元年,三月廿九日则是禹秋兰遇害的日子,也就是刘扁和古公公去韩家密会韩侂胄的那天。他看至绢帛的左下方,见到了两处字迹不同、按压了指印的署名,分别是刘扁和古晟。在这两处署名的旁边,还有一个“韦”字,上面也有些许指印,看起来应是第三处署名,只是正好位于缺失的左下角,署名也残缺了大半。虽只剩一个“韦”字,但宋慈一下子便想到了韩侂胄,那是“韩”字的右半边。虽然绢帛上没有写明,但刘扁与古公公身份特殊,一个身在翰林医官局,一个身在御药院,韩侂胄私底下与这二人密会盟誓,还写明是为了共扶嘉王,不难想象这背后存在多大的问题。宋慈知道,这便是虫达用来威胁韩侂胄的证据。然而这方绢帛被烧掉了一角,且烧掉的正好是韩侂胄的署名,单凭一个“韦”字,根本无法指认韩侂胄。
宋慈想到了净慈报恩寺的那场大火,以为这方绢帛是在那场大火中被烧去了一角。他当然不会知道,这方绢帛的左下角,其实是被韩侂胄自己烧掉的。当年韩侂胄收买了刘扁和古公公,因为担心二人背叛,于是用这一方绢帛,彻底断绝了二人的退路。但在借助绍熙内禅扶嘉王赵扩登基之后,这一方用来约束刘扁和古公公的绢帛,便已经用不上了,留着反而成为后患,于是韩侂胄打算将之烧掉,但因为刘弼的突然登门造访,这一方原本已经扔进炭盆的绢帛,最终被留守书房的虫达得到了。当时虫达看见炭盆中冒起一丝火光,只走近瞧了一眼,便赶紧拿起来拍灭火焰,这方绢帛的左下角,连同韩侂胄的大半署名,便是在那时被烧掉的。后来韩侂胄发现炭盆里没有绢帛的灰烬,猜到这方绢帛落入了虫达手中,去让虫达交出来时,反而受到了虫达的威胁。虫达因为韩侂胄得势之后只让他做了一个小小的虞候,早就心怀不满,有了这方绢帛,当然要利用起来。彼时韩侂胄还在与赵汝愚争权,不得不选择隐忍,虫达后来能手握兵权,不断获得提拔,短短三四年间,成为外镇一方的统兵大将,便是由此而始。但虫达从始至终没有将这方绢帛拿出来过,因为韩侂胄署名的缺失使得这方绢帛一旦拿出,便会失去对韩侂胄的牵制作用,反倒是不拿出来,韩侂胄并不知署名已毁,这才会处处受制。只不过虫达成为外镇一方的统兵大将时,韩侂胄也早已扳倒了赵汝愚,并利用理学之禁打压异己,牢固了自己的权位,不愿长久受此胁迫,决定召虫达入京,除掉虫达这个祸患,这才有了后来的事。
宋慈虽然不知道韩侂胄署名被烧掉的实情,但他念头转得极快,想到韩侂胄对这方绢帛如此看重,可见并不知晓绢帛上的署名缺失,只要他不拿出来,这方绢帛便依然有用。然而这个念头只是在他脑海中一闪而过,他想得更多的,则是弥音留下这个证据的举动。
弥音并不知道宋慈会找去望仙客栈,他之所以将这方绢帛埋在何太骥的墓地,是因为真的打算就这样决绝赴死。但宋慈的一再坚持,最终还是触动了他。他并不了解宋慈查案的决心能坚定到何种程度,所以没有将韩侂胄的秘密直接告诉宋慈,也没有直接告知这方绢帛的下落,若宋慈的决心不坚定,贸然将这些事告知宋慈,只会害了宋慈的性命。于是他留下了暗示,倘若宋慈连这个暗示都猜解不透,也就没有查破此案的能力,若宋慈果真有查案的决心和能力,那就一定能把这一切挖出来。他这是要让宋慈有选择的余地,让宋慈自己去决定要走的路。
站在何太骥的坟墓前,手捧着弥音埋下的绢帛,想到弥音赴死之前还能如此用心良苦,想到这对叔侄一文一武,却都选择用自己的方式,去挑战韩侂胄的权威,想到骐骥一跃,明知不能十步,却还是跃了出去,宋慈内心陡然生出一股莫大的敬意。如今这方绢帛握在了他的手中,该轮到他去抉择了。
宋慈将绢帛折叠起来,揣入怀中,在墓碑前坐了下来,一动不动。桑榆知道宋慈在想事情,静静地候在一旁。些许轻细的脚步声响起,是桑老丈见宋慈和桑榆长时间没回去,担心出事,寻上山来。桑榆轻轻竖指在唇,示意桑老丈不要出声。父女二人没有打扰宋慈,就安安静静地等在一旁,后来等得太久,便靠着一株大树坐下,裹紧衣袄,竟迷迷糊糊地一直等到了天明。
山中雾气弥漫,于一片迷蒙之中,宋慈站起身来。他已做出了决定。下了净慈报恩寺后山,来到西湖边上,宋慈说什么也不再让桑榆跟着了。他向桑榆深深一礼,转过身去,独自走入了白茫茫的迷雾。桑榆立在道旁,望着宋慈远去的背影,眼圈微红。其时西湖水雾缥缈,似笼轻纱,如诗如画。
宋慈怀揣着那一方绢帛,独自一人来到了吴山南园。面对韩侂胄摊开的手掌,宋慈没有将绢帛拿出,而是叹道:“为了得到这个证据,太师真可谓煞费苦心。新安郡主多次替我解围,还从圣上那里为我求来口谕,让我有权追查虫达一案,可我因为太师知道我奉旨查案一事,竟怀疑郡主暗中向太师告密。直到我找到了这个证据,证实了关于太师秘密的猜想,才知道告密之人是有的,但这人并非郡主。”他摇了摇头,“向太师告密的,想必是圣上吧。我原以为圣上许可我查案,还要我保守秘密,是有打压太师之意。可我查案那几日,太师一直未加干涉,甚至什么都没做,似乎有意放任我查案。其实太师也想让我去查,正好借我之手,将虫达留下的证据找出来,我说的对吧?”
韩侂胄不置可否,只是原本摊开的手掌慢慢收了回去。
“自绍熙内禅以来,十年有余,圣上一直对太师信任有加。赵汝愚身为宗室之首和文臣之首,太师能轻而易举将之扳倒;天下读书人都推崇理学,太师说封禁便封禁;北伐未得其时,太师想北伐便可举国备战。无论太师做什么,圣上始终站在太师这一边。”宋慈继续说道,“太师想让我去查案,圣上自然会许可。上元节视学那天,即便没有郡主去求旨意,我想圣上最终也会准我联名所奏,许我查案之权。虫达手中的证据,不仅对太师重要,对圣上也同样重要,要知道吴兴郡王赵抦尚在人世,倘若这个证据一直留在世上,对圣上恐怕也会有所不利。既然我有意查案,那正好顺水推舟,只需暗中派人盯着我,便知道我去过什么地方,查问过什么人,所以后来太师才能一下子将道济禅师、祁驼子、欧阳博士等人全都抓走下狱,只怕连弥音冒死行刺,太师也是事前便已知晓。自始至终,我在太师眼中,在圣上那里,不过只是一颗棋子而已。”
“圣上对此事全不知晓。”韩侂胄忽然道,“宋慈,你不要胡言乱语。”
宋慈叹道:“那就当我是胡言乱语吧。”伸手入怀,取出了那一方绢帛,并当着韩侂胄的面徐徐展开。
韩侂胄眉心一紧,那绢帛上的字迹,他认得无比清楚,正是他处心积虑想要寻找的证据。他本以为宋慈敢只身前来,必定将这证据放在了别处,哪知宋慈竟会随身带着,不免暗暗吃惊。
宋慈手持绢帛,有意捏住了左下角,不让韩侂胄看见缺失的署名,说道:“新安郡主曾对我提及,恭淑皇后一直对我娘亲的死耿耿于怀。”向手中的绢帛看了一眼,“是啊,庚戌三月廿九日,八字桥韩宅门前,若非恭淑皇后叫破刘扁和古公公的名字,我娘亲也不至于无辜枉死。我娘亲不认识刘扁和古公公,不知道这二人出入韩宅意味着什么,可一旦将此事说了出去,知道的人多了,总有人能想明白其中问题所在。太师为了这次密会盟誓,甚至让夫人和韩携仆从出城赏花,那是连至亲之人都要瞒着,哪知却被恭淑皇后、新安郡主和我娘亲撞见。恭淑皇后本就是嘉王妃,就算知道了个中原委,也不可能说出去。新安郡主彼时尚年幼,又是恭淑皇后的亲妹妹,太师不可能对她下杀手,加之又是太师的亲族,只需安排人盯着就行。至于我娘亲,一个非亲非故的外人,随时可能将此事说出去,自然不能留着。虫达之所以在我娘亲与恭淑皇后分开后,刚回到锦绣客舍之时,便潜入行香子房行凶,正是为了赶在我娘亲有机会接触其他人说出此事之前,将我娘亲杀害灭口。恭淑皇后后来应该是想明白了这些事,知道是因为她叫破了刘扁和古公公的名字,才害得我娘亲被害。可她又不能将此事说出来,连妹妹新安郡主都不能告诉,这才会对我娘亲的死心怀愧疚,一直耿耿于怀。”
听着宋慈所述,当年那一幕幕往事尽皆浮现在眼前。韩侂胄当年的确担心禹秋兰泄露秘密,这才问明禹秋兰的住处,授意虫达跟去,先摸清楚禹秋兰的来历再做打算。然而不久后虫达返回,竟说他已除掉了禹秋兰,并留下痕迹嫁祸给宋巩。韩侂胄是有杀人灭口之心,但何时动手、如何动手,他还未有定夺。虫达此举,虽说是为了替他除掉后患,却实在太过自作主张,可是木已成舟,他只能买通府衙,想方设法遮掩此案,顺着虫达留下的痕迹,要将宋巩定为凶手。但宋巩得祁驼子相助,最终洗清了嫌疑,韩侂胄担心宋巩会追查真相,这才让虫达威胁宋巩离开,并让虫达自认杀害禹秋兰是为了报复私怨,哪怕宋巩真不怕死去追查真相,到时候也可以让虫达去顶罪。韩侂胄嫌虫达擅作主张,从此渐渐开始疏远虫达,虫达对韩侂胄暗怀不满,生出异心,同样也是源于这件事。
但韩侂胄没有向宋慈解释什么,也没必要找借口为自己开脱,他只道:“你到底想做什么?”
他盯着宋慈,心想宋慈敢直截了当地拿出那方绢帛,还敢如此肆无忌惮地说出一切,想必早就留了后手。他想到了杨皇后,想到了杨次山,想到了朝堂上的一干政敌,甚至想到了圣上。环顾整个归耕之庄,四下里空无一人,忽然之间,他竟生出了一丝如芒在背之感,仿佛有万千刀斧手正埋伏于四面八方。他的手向外伸出,慢慢按在了剑柄上。
宋慈摇了摇头,道:“我别无他意,只想说出我查到的一切。”
说完,宋慈向墙角走去,将那一方绢帛丢进了用于取暖的炭盆之中。火光亮了起来,那方绢帛连同上面的文字,在猩红的火焰之中,慢慢地化为灰烬。
韩侂胄皱起了眉头,很是费解地望着宋慈,按在剑柄上的手,慢慢地放开了。
昨晚在净慈报恩寺后山,宋慈静静地坐了一夜,也想了一夜。他手握那一方绢帛,有着太多太多的选择。他可以返回提刑司,请乔行简召集官吏民众,出示这方绢帛上的盟誓,像之前查破那几起命案一样,当众揭开虫达一案的秘密,揭开母亲枉死的真相。又或者,他可以将韩侂胄的秘密公开,太学有那么多学子对韩侂胄不满,只要他将这秘密连同绢帛上的盟誓写下来,一夜之间便可动员众多学子抄写成百上千份,连夜散发全城,天亮之后,这秘密便会传遍临安,不久便将传遍天下。再或者,他可以将这方绢帛交给杨次山,杨次山有杨皇后撑腰,一向与韩侂胄势同水火,得到这方绢帛,就算上面署名有所缺失,想必也能大做文章,定会给韩侂胄带来不少麻烦。但是无论怎样,这秘密事关当今圣上,他不能就这么公之于众。他也终于想明白了,当初虫达、弥音和何太骥等人为何不公开这个秘密,想必也是因为牵涉圣上。譬如虫达,宁肯隐姓埋名出家为僧,坐视家眷坐罪受罚,也始终没有公开这个秘密,只因他一旦这么做,就算能扳倒韩侂胄,也会因为牵连圣上,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。虫达根本不在乎自己的家眷,哪怕早已得知他的一双女儿在临安城里为婢为妓,近在咫尺的他,也从来没有设法去帮过自己的女儿。对他而言,自己的性命胜过一切,他藏身在临安城郊,那是为了等待机会,只有当朝局出现剧烈动荡,或是皇位出现更替之时,他才会公开这个秘密。与虫达相比,宋慈不惧一死,但他心如明镜,知道这秘密一旦公开,必定朝野动荡,要知道吴兴郡王赵抦尚在人世,别有用心之人说不定会趁机作乱,届时局势很可能比绍熙内禅之前更加混乱,一旦酿成兵灾人祸,承平数十年的大宋,只怕会陷入一场莫大的浩劫。
宋慈来到临安,名义上是为求学,实则在他内心深处,从未忘过母亲之死,查明母亲遇害一案的念头,已在他脑中根深蒂固十五年。如今他查明了一切,终于有机会为枉死的母亲讨回公道,然而他却犹豫了。一己之公道,与天下百姓之太平,孰轻孰重?一夜过去,他想明白了,于是只身一人来到了吴山南园,揭开母亲枉死的真相。他知道这根本算不上公道,但他只能这么做,哪怕他不愿如此,哪怕他要和父亲一样,永远背负对母亲的愧疚。
“往昔绍熙内禅,流言四起,人心惶惶,变乱丛生。圣上登基十年有一,一切早成定局,大宋也已重归太平,如今少一人知道这个秘密,世上便能少一份灾劫。此间别无旁人,太师可以说我图谋行刺,当场将我诛杀,世人也许会有所非议,但过不了多久,便会没人在乎,没人记得。”宋慈说道,“刘克庄、辛铁柱,还有其他因太师遇刺被下狱之人,他们都不知晓太师的秘密,望太师在我死后,能将他们放了。大宋承平不易,天下难安,还望太师整军经武,善择良将,得其时机,再行北伐。”说罢,他立在原地不动,缓缓闭上了眼睛。
韩侂胄直到此时,才算明白了宋慈为何会做出种种异举,道:“原来你是求死来的。”冷淡一笑,“我以为你只会认死理,想不到你也有放弃的时候。”
宋慈是为天下所计,方才烧掉了那一方绢帛,在最后一刻放弃了追查到底。韩侂胄竟隐隐然为之触动。他掌权十年,大可贪图享乐,却一心北伐,志在恢复中原,又何尝不是为天下所计?宋慈不惜得罪他,受尽各种阻挠,冒着身死命断的危险,一直查案至今,那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,而他用尽手段,从一个韩家的旁支外戚,一步步走到今天,只为建那不世之功,留那万世盛名,又何尝不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?宋慈只是一个小小的太学生,身无尺寸之柄,为了追查亡母一案的真相,一路走来受过多少冷眼,付出过多少代价,只有宋慈自己知道,而他又何尝不是如此?他原本只是一个恩荫武官,始终被那些科举出身的朝臣看不起,以至于年过四十,还只是一个小小的知閤门事,那些把控大权的朝臣只知贪图安乐,不思进取,让他看不到任何建功立业的机会。他可以只做武官,可就算他把武官做到头,又能如何?他不想像岳飞那样,矢志北伐,却被朝臣掣肘,被圣上猜忌,以至于功败垂成,受那千古之冤。唯有不择手段,将大权揽于一身,才有机会去实现自己的抱负。这一路走来,付出过多少代价,跨越过多少阻碍,只有他自己知道。朝堂上那一帮帮腐儒,只知道阳奉阴违,从来不知同心齐力;太学里那一批批学子,只知道与他唱反调,从来不会建言献策;家中独子鼠目寸光,只知道飞扬跋扈,从来不懂为他分担;他容忍过虫达,放任过刘扁,可这些人不知收敛,反而只知道得寸进尺,变本加厉地威胁他;原本以为除掉了虫达和刘扁,从此便可高枕无忧,哪知突然又冒出来个何太骥,竟敢明目张胆地要挟他;他以为何太骥是从刘鹊那里获知的秘密,派夏震助李青莲缢杀何太骥的同时,逼迫刘鹊交出虫达留下的证据,哪知刘鹊宁肯自尽也不交出来,他这才意识到证据不在刘鹊那里,于是当得知皇帝已口谕宋慈追查虫达一案后,他便暂且留了宋慈一命,想着借助宋慈之手,将与虫达相关的人和证据都挖出来。他想尽办法试图抹掉的证据,如今终于在他眼前化为灰烬,十年来的忐忑不安,至此终于可以放下。
但是他想不明白,自己执掌天下权柄,明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,为何这些人总是不知天高地厚,一个个地跳出来与他作对?为何自己身边尽是赵师睪这等溜须拍马之辈,如乔行简那般有真才实干的官员,明明是他亲手提拔起来的,却总是莫名其妙地站到他的对立面?为何何上骐那样的忠勇之士,宁肯剃度出家,隐姓埋名,甚至抛却性命来行刺于他,只为报效虫达,却不肯效忠于他?更有宋慈这般心志坚定、身负大才之人,却终究不能为他所用……他好长时间没有说话,就那样看着宋慈,心中想了太多太多。
“你走吧。”不知过了多久,韩侂胄开口了,“你这样的人,与我倒有几分相像,杀了实在可惜。刘克庄、辛铁柱那些人,只要不再与我作对,我会放了他们。你走之后,我会一直派人盯着你。我在朝之日,或者说当今圣上在朝之日,你就别想再为官了。你所负之才,就留给下一朝吧。”
宋慈一心求死,静待刀剑加身,听得此言,睁开了眼睛,有些诧异地看着韩侂胄。韩侂胄不耐烦地挥了挥手,唤入夏震送宋慈离开,尤其叮嘱不是送宋慈离开南园,而是送宋慈离开临安。他本人则站起身来,拾起那柄宝剑,独自步入后堂,只留下那一只已经冰凉的手炉孤零零地摆放在原处。
宋慈不再多言,向韩侂胄的背影行了最后一礼,转过身去,走出了归耕之庄。
临安城的这场雾,长久没有散去,直至正午将近,仍是蒙蒙的一片。
清波门外,西湖岸边,宋慈与桑榆告别,准备回建阳了。他没有回太学收拾行李,那些书籍衣物,已没有带回去的必要。宋巩已雇好了车,在城门外等着他。夏震带着几个甲士站在城门旁,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他。
桑榆朝府衙的方向遥指一下,比画了见面的手势,脸上带着不解之色。
她是问为何不等刘克庄和辛铁柱出狱,见过面之后再走。他摇了摇头。他不愿对刘克庄和辛铁柱有任何隐瞒,可韩侂胄的秘密是什么,虫达留下的证据又是什么,他又不能对二人说出来。他心里明白,韩侂胄能放过他,不一定能放过别人,刘克庄又是他的至交好友,与之再有过多接触,难免韩侂胄不起疑心。所以相见不如不见,之前司理狱中那一面,就当是最后一面吧。他托桑榆等刘克庄和辛铁柱出狱之后,帮他带一句话,让他们二人永远不要去建阳找他。
除此之外,宋慈把所有的钱财留给了祁驼子。宋巩当年受虫达威逼,为了保护年幼的宋慈,不得不匆忙离开临安,没来得及报答祁驼子的救命之恩,更不知道祁驼子后来的遭遇,十五年后重回临安,才从宋慈那里得知了一切。宋巩很想再见祁驼子一面,当面感谢祁驼子的莫大恩德,但如今祁驼子身在狱中,他父子二人又不得不立即离开临安,这一面,也不知此生还能否见得。为救宋慈,宋巩带来了不少钱财,包括家中的全部积蓄,以及典当家当所得的银子。他明白这些钱财远远抵不得祁驼子所遭遇的一切,但他此时能做的只有这些。将来若有再回临安的机会,他一定会去见这一面的。
桑榆不认识祁驼子,宋慈请桑榆把这些钱财交给出狱之后的刘克庄,让刘克庄代为转交。祁驼子的恩德,宋慈会一辈子铭记,还有因他入狱的叶籁、欧阳严语等人,他会始终感念在心,至于韩絮的死,恐怕他终此一生,也不得释怀了。
桑榆还有行李留在梅氏榻房,要等收拾完后,才会离开临安返乡。临别之际,她将藏在袖子里的东西取出,轻轻放到了宋慈的手里。那是一个半尺高的人偶,是她为了感谢宋慈的救命之恩,用了好长时间亲手刻成的,之前因为宋慈突然入狱,她一直没有机会送出。
那人偶是照着宋慈的模样刻成的,还细细地涂上了颜色,形神兼具,惟妙惟肖,活脱脱便是一个小宋慈,只不过与宋慈平日里的不苟言笑比起来,那人偶弯起了嘴,大方地笑着,多了几分可爱。
宋慈将那人偶握在手中,看了又看。他道一声“多谢”,向桑榆告了辞,登车而去。
第十一章 尾声
重回建阳,已是二月中,宋慈离开一年,家乡的一切都没变样,可他却有恍如隔世之感。
不久之后,桑榆回到了建阳。桑榆告诉宋慈,他离开临安后的第二天,刘克庄、辛铁柱、祁驼子、欧阳严语和道济禅师等人都被释放出狱,连叶籁也免罪获释。桑榆把宋慈留下的钱财交给了刘克庄,请刘克庄转交给了祁驼子,也把宋慈的话转告给了刘克庄,刘克庄先是愣了愣,随即放声大笑。桑榆比画手势问刘克庄笑什么,刘克庄说是因为高兴。其实在刘克庄的心中,最在意的从来不是什么真相,而是宋慈的安危。只要宋慈平安无事,对刘克庄而言,那就是最值得高兴的事。刘克庄还笑着对辛铁柱道:“宋慈这小子,一辈子那么长,他说永远不见便不见吗?”
刘克庄又拉上了辛铁柱和叶籁等人,也请了桑榆,同去琼楼大饮了一场。席间辛铁柱提及,他已决定参军戍边,沙场报国,刘克庄兴奋不已,当场赋诗痛饮,为辛铁柱壮行。在场人人都看见,刘克庄这一场酒喝得极为尽兴,醉到不省人事,但没有人看见,刘克庄醉倒之时,闭上眼的那一刻,眼角流下了泪水。
得知刘克庄和辛铁柱等人尽皆平安,宋慈欣慰一笑。
此时的宋慈还不会知道,短短三个月后,吴兴郡王赵抦薨逝,同月,韩侂胄奏请皇帝下诏伐金,并告于天地、宗庙、社稷,兵发三路,正式大举北伐。然而金国早有准备,三路宋军皆告失利,金军乘胜分九路南下,短短一年时间,樊城失陷,襄阳告急,淮南多地沦陷,四川宣抚副使吴曦叛变称王,金军甚至已饮马长江,形势岌岌可危。朝廷不得已遣使向金国求和,金国提出要斩韩侂胄等人方可罢兵,韩侂胄自然不答应,筹划再战,随后襄阳解围,吴曦之叛被平定,淮南局势渐趋平稳,形势开始好转。就在这时,史弥远与杨皇后、杨次山等人密谋,伪造皇帝御批密旨,指使夏震在上朝途中将韩侂胄斩杀于玉津园夹墙内,事后才奏报皇帝。韩侂胄的头被割下,函首送往金国求和,是为嘉定和议,朝堂大权自此渐渐落入史弥远之手。韩侂胄的下场,也算应验了那一方绢帛上“违誓背盟,不得其死”之语,在他死后,原来依附于他的那些党羽,可谓树倒猢狲散,其子韩则被削籍流放沙门岛。
眼下宋慈还预料不到这些变故,但史宽之能在泥溪村遇袭前向他告密,之后还向他索要虫达留下的证据,就连杨次山也曾向他讨要这个证据,可见韩侂胄的身边早就被安插了眼线,而且这个眼线能获知如此秘密之事,必定是韩侂胄的亲信之人。但他离开吴山南园时,没有将此事告诉韩侂胄,只是提醒了韩侂胄不要仓促北伐。
时隔一年,宋慈终于又来到了母亲的墓地。他本以为今年回不来的。与往年一样,他独自一人静静地坐在坟前,从日出到日暮,陪了母亲一整天。
“慈母手中线,游子身上衣”,宋慈的名字,是母亲为他取的。在禹秋兰的想象中,自己的儿子,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好男儿,会有天开地阔的志向。她知道宋慈总有一天会离家远行,每年都会亲手为宋慈缝制新衣,然而十五年前锦绣客舍里那件布彩铺花的新衣,却成了最后一件。她意恐宋慈迟迟归,如今宋慈归来了,可她早就先行一步,永远不再回来。
墓地旁边,当年禹秋兰下葬之时,宋慈和父亲宋巩亲手种下的那株桃树,如今已长高长大,花开正好。晚风摇林而过,时有花瓣随风而下,轻轻飘落在宋慈的身上。宋慈抬起头,朝那枝头看去。当年没能与母亲一起去看的那场桃花,如今年年岁岁,都在眼前。
(第一季完)
宋慈洗冤笔记4(出书版) 第17节
同类推荐:
因为手抖就全点美貌值了[无限]、
麻衣神算子、
楼前无雪、
阴差阳做、
百合绽放、
宅师笔记、
人间生存办事处、
租鬼公司、